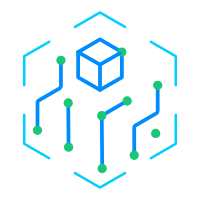区分志贺菌和伤寒沙门菌(布惊菌与不惊君)
丘艳荣翻开菜园围墙根下的落叶堆,一长溜半撑着小伞的布惊菌出现在眼
丘艳荣翻开菜园围墙根下的落叶堆,一长溜半撑着小伞的布惊菌出现在眼前一顶顶灰褐色、浅土色的布惊菌像没睡醒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防备,就被我猛掀了被窝,然后装进菜篮,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区分志贺菌和伤寒沙门菌?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区分志贺菌和伤寒沙门菌
丘艳荣
翻开菜园围墙根下的落叶堆,一长溜半撑着小伞的布惊菌出现在眼前。一顶顶灰褐色、浅土色的布惊菌像没睡醒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防备,就被我猛掀了被窝,然后装进菜篮。
这时,屋里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挎着满篮子布惊菌的我飞快从后门跑进了屋,接生婆正好端着脸盆出来,她笑着对我说:“阿妹,你当姑姑了。”那天,是侄女珊珊出生的日子。清晨的阳光从屋后的龙眼树缝里探头探脑地投射进来,跟九岁的我一样好奇。我在嫂子挂着门帘的房门口晃来晃去,很想看看那个叫我姑姑的小婴儿长什么样。
后来,珊珊成了我的“小尾巴”。夏日的清晨,她跟着我到屋后采布惊菌。我们把落叶踩得沙沙作响,双脚沾满初夏的清新味道。竹林里、龙眼树下,每一寸地方我们都不曾放过,细细查看,细细翻检,可就是再没有碰到过如珊珊出生那天那样的好运气了。我便对珊珊说:“可惜了,有你这顶大布惊菌在,那些小布惊菌就不肯出来了。”她长得白白胖胖的,确实像一顶胖胖的布惊菌。珊珊不服气地说:“姑姑是超级布惊菌,小布惊菌才不肯出来了。”
“布惊菌”是我们当地的叫法,后来我才知道它叫鸡枞菌、鸡肉菇,也叫伞把菇。这几种叫法我还是很认可的。“伞把菇”是取其形,“鸡枞菌”“鸡肉菇”应该就是取其味吧。布惊菌肥硕壮实、质细丝白、鲜甜脆嫩、清香可口,可与鸡肉相媲美。所有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布惊菌是菌类中的上品,野生布惊菌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如今回忆起它的鲜美竟有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联想。确实,美味的布惊菌是可以跟仙乐等同起来的。
记忆里,布惊菌的吃法非常简单。把布惊菌洗干净,将菌顶撕成块,菌脚撕成丝。那洁白柔韧的丝与块让人联想到手撕鸡肉,于是便对将下锅的布惊菌平添了几分期待。因为每次收获到的布惊菌都不多,所以通常用它来煮汤。把清水与切成段的咸菜、三两片薄姜一起下锅,咕噜噜煮开,等姜的香味和咸菜的香味钻入鼻孔,唤醒蠢蠢欲动的味蕾时,就把清洗干净的布惊菌放入锅,煮上几分钟,加点盐,撒点胡椒粉,就是鲜美无比的布惊菌汤了。偶尔遇到家里割了点肉,就会煮一大碗瘦肉布惊菌汤,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奢侈享受了。那汤,鲜到了极点,两碗白米饭拌着汤下了肚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珊珊出生那天采到的布惊菌比较多,所以难得炒了一次。咸菜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也是布惊菌的最佳伴侣。把蒜蓉用热锅热油爆几下,再把咸菜段、薄姜片下锅炒一炒,最后放布惊菌混着炒,除了少许盐,多余的配料都不需要,一盘又鲜又下饭的清炒布惊菌就完成了。
后来,我还是会在夏日的清晨到屋后的落叶堆寻找布惊菌的踪迹,有时能找到几顶,有时一无所获。再后来,要依仗双拐行走的我已不便在青藤遍地、瓦砾成堆的屋后行走了。我有一次问母亲,屋后还有布惊菌吗?母亲说,后面的竹子砍了,龙眼树也砍了,没有落叶堆,也就没有布惊菌了。
突然想起小时候问过母亲的问题:阿妈,“布惊菌”为什么叫“布惊菌”?母亲随口说,可能是给它取名的人刚好在布惊树下捡到了它吧。这个假设让我无从反驳,我也就姑且认同了母亲的说法。
后来,我翻书时偶然看到关于“布惊”的传说:据野史记载,唐末藩镇纷争,中原战乱,民生凋敝,百姓无以为生。客家祖先为避战乱举家南迁,因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瘟疟盛行,无医少药,只能哀哀待毙。一日,空中降一神鸟,身披五彩,眩然如日,鸣声若“不惊,不惊”,似有抚藉众生之意。神鸟爪踏之处,皆化为葱荣木林,其叶鲜嫩,清香扑面。客家人采而生嚼,或加汤热饮。不久,瘟疟自除,客家人得以安然南迁。后客家人称之为“布惊茶”,不论身在何处,都怀藏布惊。
这个有些偏题的发现却让我得到了某种抚慰一般:“布惊菌、布惊菌……”我喃喃地念。然后,我脱口而出“不惊君”,说完自己也傻笑了起来。好吧,从此以后我就叫自己“不惊君”吧!读一遍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拄着拐杖又何妨,风雨人生又何惧?慢慢走,不用怕。
珊珊,姑姑真的成了一顶“布惊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