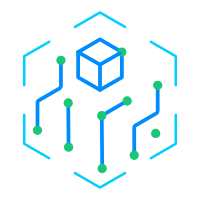一程山水一壶乡愁(不过一页地瓜干)
文/夏德明
01
提起地瓜干,上了年纪的五莲人大都百感交集吧。

01
提起地瓜干,上了年纪的五莲人大都百感交集吧。
饥也瓜干,饱也瓜干;苦也瓜干,甜也瓜干;爱也瓜干,恨也瓜干。
瓜干,承载着村庄一代又一代人沉重的乡村情感。
那些从村庄出走的少年、青年,谁会轻易地忘记瓜干呢?谁会嫌弃、背叛过瓜干呢?
那些极个别背叛了瓜干的,大概都出事了吧。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秋季思瓜干。
如果乡愁能晒干,你会发现不过是一页瓜干。
02
我在《面条||洁白柔软的身段,是多少穷孩子的梦想》(点击阅读)中写道:
“ 年轻的奶奶要改嫁,偷偷抱着年幼的父亲跑了。刚到诸城,被得知消息的族人赶去拦截下来。 父亲被抱回来,成了孤儿,寄养于叔伯兄弟。”
父亲终于长大成人,婚后还是和叔伯大哥家一个锅里摸勺子。
正月15,我的大爷就去借地瓜干;正月22,娘生的我。
大娘把几页借来的地瓜干浸泡,上锅馏了,端给我的娘在炕上吃。其余一家人----父亲,大爷大娘,叔伯大哥、小哥、大姐、小姐姐,在当门里喝稀糊嘟。
(其实,我称大爷、二大爷为爷,称大娘为娘,称二大娘为亲娘~~二大爷当年一表人才,但不顾家人反对,取了寡居的大娘,未曾生育,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一致称她“亲娘”)
娘招呼最小的、四五岁的二哥,一起吃瓜干。二哥拿着一页,张扬着,兴高采烈地咀嚼、品尝。
大娘大声斥责我的娘:“依着他吃得吃多少!”阻止给她的亲生儿子吃瓜干。
~~过去快60年了,这一句“依着他吃得吃多少!”,娘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不差;那语调也能模仿出来。
几年之后,我的大姐出息成人了,个子高高,俊俏模样,是村里有名的一枝花,那可真是“要样有样,要活有活”,但被我的大爷嫁给户部黄巷子村陈家做妻,换回了一提篮地瓜干。
大姐嫁的男人,相貌、体质、能力皆不及一般,又老实,懦弱,实在配不上大姐。我实话实话,也不怕他知道了。
大姐一辈子过度操劳,自然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现在已是风烛残年,每次去看她,她还忘不了和我谈那一提篮瓜干。
大姐夫~~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称他姐夫,一直称表哥~~在一旁嘿嘿的笑。
就凭那一提篮地瓜干,一家人暂时度过了难关。
生活慢慢好起来,就不需要用漂亮的二姐换地瓜干了。
二姐是自由之身了,嫁给邻村小于子一户姓丁的好人家,二姐夫吃国库粮,人也帅气,聪慧伶俐,知书达理。
村里的识字班都羡慕嫉妒恨,但有什么用?有的爷娘还指望着她换地瓜干,或者给她哥哥换个媳妇。
03
上周末,爱人买回一袋子地瓜。我问多少钱,她说9毛。
我感叹太便宜了,并有些心酸:你从田里运一些土块来城里售卖,也少不了9毛啊。
因为我知道,种地瓜,就像是村里养个孩子。
翻土,筑垄,育苗,插秧,施肥,浇水,掐秧,翻秧,一遍遍的除草~~每一个步骤都可以累你个半死。
最后地瓜被一撅一撅地刨出来,一排排的,像残兵败将,仰面朝天,等待命运安排。
从地瓜到地瓜干,还一段考验体力与智慧的农活。
切瓜干是最吃力的。最老式工具,像切片的“擦窗”,用手拿着地瓜来来回回地擦。
后来有了专门切瓜干的“铡”。
摇铡最累,只能换着人摇。如果速度、力度达不到,就会卡壳。
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少年纷纷请战,纷纷败下阵来。
我也在其中,也愧对“少年强则中国强”。
晒瓜干,最怕下雨天、连阴天,很容易“晒”成眼镜。
腐烂,发霉,变质,只能喂猪,但这是猪的硬菜。
也许,刨地瓜的那些日子,村里的猪们天天仰望星空,祈求阴雨连绵。
据说,一等生产队队长、家长料雨如神,避开雨天;二等的,听天由命;三等的,也是料雨如神——何时晒瓜干何时下雨,不早不晚,于是就有“他大,xx家今日晒了,咱别跟着”的笑谈。
晒瓜干,一页页地避免重叠地摆放,倒退着摆放,双腿最累。
“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
活是这么个活,但没有这么诗情画意。
至于摆放的地点,最上是山脚的石板。
石板少,必须要早早抢占。
你看见石板中央有一撮地瓜秧,被石块压着,就意味着名花有主了。
其次是干涸的河床。
宽阔平坦,运输摆放方便,但有暴雨之忧。
最下的田间地头。
土壤刚刚翻出,地面潮湿,不易晾晒,非艳阳高照、懒到极致不会出此下策。
那时节,远望去,从山脚,到田间,再到河床,这儿一片,那儿一片,断断续续。
村庄就是瓜干的大晒场。

04
拾地瓜干,也是麻烦事。
半夜破锣声撕裂地响起,“到xx拾瓜干喽”,“所有人员,妇女,孩子,都去!”声嘶力竭,惊恐万状,如大难临头。
天有不测风云,原来是大雨突降。
在河床,没有灯光,人影憧憧,都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凭手感捡拾瓜干,与流水争抢。
那时我很小,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常常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遇到一直风和日丽,那是“老天有眼”。
妇女、孩子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拾瓜干。
男人则去干重活了。
最后,漫坡遍野地去拾瓜干皮,交给学校,称一称,记在本子。多的,开学后能发一个演草本。

05
在村庄,瓜干好像是略小几圈的钢镚,是无法折叠的纸钞。
我还记得,大榆林村张见友家用瓜干换陈姓人家的麦子的情形。
好像是一兑一吧,只因为瓜干充饥,紧吃——吃饱永远高于吃好。
那时,张是村里的供销社售货员,是响当当的人物,后来一度当过村主任。村里的第一口压水井,就是他家打的,我在一旁看热闹。
我接到大学通知书之后,沾亲带故的,他拿着一盒大前门去我家,父亲高兴地请他喝酒。
如今他离世很久了。有时路过他的家门口,我就会想起一些他的故事来。
我还记得,一帮伙伴商量凑瓜干换豆腐吃,每人从家里偷几页,只有一名伙伴说,他家的瓜干密封得严严实实,实在插不进去手~~其实,他是怕挨揍,他老的下手最狠~~逼得他在木杆上绑上袜子,偷大队粮囤里的瓜干。
我还记得,馋媳妇偶尔用瓜干换块豆腐,妇女、老人就会在她背后指指点点:“不过日子。”
我还记得,要饭的上门,便送一页、半页瓜干。

06
瓜干可以熘了吃,煮了吃。
可以磨成面,包包子,擀面条。
最普通、最经典的吃法是烙煎饼。
瓜干用大盆浸泡一天一夜,捞到大黑锅里,一刀一刀地剁碎~~哪个60、70后小时候没干过?
再用石磨磨成面糊。推磨最愁人~~哪个60、70后小时候没干过?
我最讨厌推磨~~一圈一圈地转,一圈一圈地磨洋工。
驴子蒙眼是不是不累?我就闭上眼睛,还是累。
只是眼不见石磨为净。
其实最累的还是烙煎饼的女人。
在热气腾腾的鏊子面前,一坐就是半天,挪动不得。
将面糊团出球状,捧到热鏊子上,拍打着滚动,一圈一圈涂满;再拿起刮板蘸水,一抿一刮,就揭下来一张薄如纸张的煎饼。
那一张张纯手工制作的、散发着瓜干又香又甜的煎饼,喂饱了我们的童年少年。
即使走出村庄,人到中年,人到老年,那味道依旧经久不散,在记忆深处。
你现在拿起一张瓜干煎饼,随便卷点什么,
就能咀嚼出一些乡愁。
夏德明:山东日照人,大学本科,正高教师,擅长散文写作。本文选自公众号《渔舟之唱晚》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