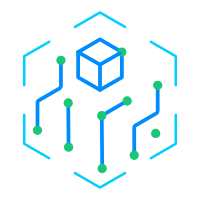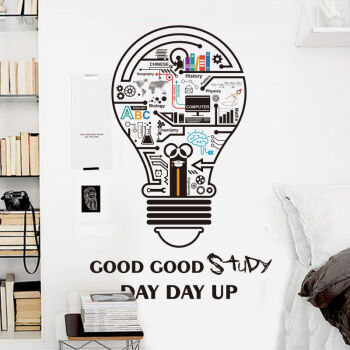名人读书故事
【名人读书故事】
在人间(节选自《在人间》 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楼适夷译。)
高尔基使我 兴的,是老婆子搬到婴儿室里睡去了,因为保姆
名人读书故事
【名人读书故事】
在人间(节选自《在人间》 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楼适夷译。)
高尔基使我 兴的,是老婆子搬到婴儿室里睡去了,因为保姆老是喝醉酒。维克托不打扰我,他每晚等家人们都睡静之后,就悄悄儿起来把衣服穿好,溜到外边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天亮才回来。晚上还是不让我点灯,因为大家都把蜡拿到寝室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便偷偷把蜡盘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灯芯,便点起一盏烟气腾腾的灯,整夜放在炉子上。
当我翻动一页书的时候,那昏红的火头就摇晃不定,好像要熄灭的样子。灯芯常常滑进燃得很难闻的蜡油里;油烟熏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读说明的快乐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一天天扩大起来的世界:这里有梦一般的城市,有高山和美丽的海滨。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更富于魅力:人多起来了,城市增加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多样,无所不有。现在,我望着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已明白那儿并不是一片荒漠,而在以前,当我遥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特别的烦恼:草场平坦地扩展着,披着破衣似的黑色灌木丛,草场的尽头矗立着参 不齐的茂密森林,草场上空展开一片混浊寒冷的蓝天,大地空旷而凄凉,我的心也空落落的,一种淡淡的悲愁,撩乱着它。我失去了一切希望,感到百无聊赖;只想闭上眼睛。这种忧郁的空虚没有给我半点希望,它只是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吸尽了。
图片的说明,用一种容易懂的文字,把另一些 和民族的状况告诉了我,把古代及现世的许多事情讲给我听,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我所不懂的,这使我感到苦恼。有时候一些奇怪的名词刺到我的脑子里──什么“形而上学”“千年天国说(千年天国说:早期 教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相信 第二次来到人间后,在世界末日之前,他将在人间建立千年的“天国”。)”、“ 运动者( 运动者:19世纪英国最早的群众性和 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活动家。)”一类奇怪的名词,对我实在有点头痛。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阻止我的想像的怪物。如果我弄不清这些名词的意义,也就永远再也不会明白什么了──正是这些名词像卫兵一样把守着秘密之宫的大门。有时候,全部的句子像扎进手指的刺一般在我的记忆里停留很久,使我再也不能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念过这样的怪诗(怪诗:指波兰诗人约·波·扎列斯基(1802—1886)写过的一部抒情长诗《草原的精灵》(1836)。1877年俄译者译了该诗的一个片断,题为《阿底拉》。高尔基这里是凭记忆写下的,因此引文不尽正确,如“在无人境中行走”一句应是“像毛茸茸的壮实的熊那样行走”。):
匈奴族的酋长阿底拉(阿底拉:是五世纪匈奴民族的酋长,曾征服高卢,以进行残酷 著称。)骑着马,满身披着钢铁甲胄,像坟墓般地阴郁和沉默,在无人境中行走。
他的背后有一队乌云一样的大军在追寻着叫喊:“何处是罗马?何处是雄伟的罗马?”
我已知道罗马是一座都城,但是匈奴是怎样一种民族呢?我必须把它弄明白。
我找到一个好机会,就向主人问。
“匈奴?”他惊奇地重复了一句。“ 知道这是什么呀?大概是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吧……”
他不西藏地摇了摇头。
“你满脑子都是些无用的东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呀,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事坏事,可是我要知道它。
我觉得团队里的牧师索洛维约夫一定会知道匈奴是什么,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他,就拉住他问。
他体弱多病,红眼睛,没眉毛,黄须,脸色苍白,性情暴躁。他把黑手杖拄着地,对我说: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涅斯捷罗夫中尉恶狠狠地回答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这个问题得去问 房里那位 剂师,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 。
“匈奴,” 剂师巴维尔·戈利特贝格对我说。“匈奴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再没有这个民族了,现在已经绝种了。”
我觉得难过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已经绝种,而是因为把自己烦恼了这么久的那个词的意思,原来只是如此简单,而且使我一无所获。
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为这个名词大伤了脑筋之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由于这位阿底拉,我跟 剂师戈利特贝格接近起来了。
这个人能够很通俗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把开启一切知识之锁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把透视正一正,从厚玻璃片中盯住我的眼睛,好像拿一些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一般,对我说:
“好朋友,一个名词好像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
我常常到那 房里去,为那些害慢性“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 ,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像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 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像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
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伦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 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庞逊·德·泰尔莱利(1829~1871):法国作家,著有多卷的《罗坎博尔历险记》等惊险 。〕、蒙特潘、扎孔纳〔皮埃尔·扎孔纳(1817~1895):法国惊险 作家,著有《一个警察局密探的手记》等 。〕、加博里奥〔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法国侦探 创始人之一。〕、埃马尔〔格卢·埃马尔(1818~1883):法国作家,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征服者为主题的惊险 。〕、巴戈贝〔巴戈贝(1821~1891):法国惊险 作家。〕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像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
“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爆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 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 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像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像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 ”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 ”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像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像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个店主,可是他也比我所知道的一切店主都好。就是书中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要亲切得多,对人更富于同情心。总之,照书上看来,外国的全部生活,比我所知道的要有趣得多,轻快得多,好得多。在外国,没有那样多的野蛮的打架,没有像捉弄维亚特兵士那样厉害地捉弄人,也没有老婆子那种狂暴的祷告。
尤其显著的,是书中虽讲着一些恶徒、吝啬 、无赖汉,但是决没有我所熟悉的和常常见到的那种说不出的残酷,以及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徒虽凶,但都凶得有道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凶,原因大体可以明白。可是我所见的那种凶恶的行为,却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可以因此得些什么好处,仅仅是为了发泄而已。
每看一本新书,这种 生活与外国生活不同的地方愈加明显,使我产生茫然的懊丧,怀疑这些角边肮脏、纸页泛黄的念旧了的书的真实性。
这时候,忽然得到了龚古尔〔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的一本叫做《桑加诺兄弟》的长篇 ,我花了一整夜一气念完了。我很惊奇,这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于是我又把这平凡伤感的故事重新看了一次。这本书里,并没有错综复杂的东西,表面上没有什么趣味。开头几页跟圣贤传一样,生硬枯燥,用语很准确,毫无一点夸张。一开始引起我一种不愉快的惊奇感,可是用朴素精练的句子组织起来的文章,却很好地记在我心里了。马戏师两兄弟的悲剧,一步紧一步地发展开来。我的两手,不觉因为看这本书的快乐而发起抖来。念到那跌断了两条腿的不幸的艺人爬到阁楼上去,而他的兄弟,正在这阁楼上偷偷地练习自己心爱的技术,这时候,我大声哭起来了。
我把这本好书还给裁缝妻子的时候,要她再借些这样的书给我。
“为什么要这样的书呢?”她轻轻笑着反问。
她这一笑把我窘住了,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书。她说:
“这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等一等,我拿一本更有趣味的给你……”
几天之后,她借一本格林武德〔格林武德(1833~1929):英国作家。〕的《一个小流浪儿的真实故事》给我。这书的书名就有点刺痛我,可是打开 页,立刻在心中唤起了狂喜的微笑,而且我一直含着这样的微笑把全书念完,有些地方还念了两三遍。
原来即使在外国,有时也有过着这样艰苦生活的少年!唔,我的生活并不那样坏,这就是说,不必悲观失望。
格林武德鼓起了我很大的勇气。在读过这本书以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本叫《欧也妮·葛朗台》的书,这已经是一本真正的“正经书”了。
葛朗台老人使我很清楚地想起了外祖父。很可惜,这书篇幅太小,可是叫人惊异的是,它里边却藏着那么多的真实。这是我生活中熟悉并使我讨厌的真实,这本书,却以一种全新的没有恶意的、平和的笔调表现出来。从前我所看的书中的人物,除了龚古尔,都是些跟我的主人们一样厉声厉色指责人家的人;那些书常常引起人们对罪人的同情,对善人的气恼。他们虽然费了很多脑筋,很大的意志,可是总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看了这种人,我总觉得有点可怜。这是因为善良的人从 页到 一页,跟石柱子似地一动不动,虽然所有一切的恶计,碰上这些石柱子都破碎了,但石柱子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一道墙,不管它怎样美丽、怎样坚固,可是当一个人要到这墙后边的苹果树上去摘苹果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欣赏这道墙了。所以我总觉得最珍贵、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后面的……
在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等人的 里是没有善人,也没有恶人的,而有的只是一些最最生动的普通人,只是精力充沛得令人惊奇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照原样说和做的,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我明白了“好的,正经的”书,能使人得到多么大的欢喜,可是这种书我到哪儿去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