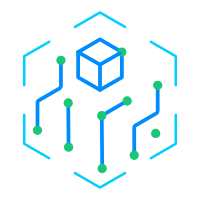回忆以前想说什么(人们如何样回忆过去)
科幻小说家特德·姜写过一部小说《双面真相》,说的是西方探险队深入一
科幻小说家特德·姜写过一部小说《双面真相》,说的是西方探险队深入一个原始部落,发现此地的人们因为不使用文字而缺乏“历史”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记忆依赖口口相传由于难以长期保留历史,部落里的时间是循环行进的这则小说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前文字时代记忆方式的“缺陷”,但这些记忆方式其实也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回忆以前想说什么?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回忆以前想说什么
科幻小说家特德·姜写过一部小说《双面真相》,说的是西方探险队深入一个原始部落,发现此地的人们因为不使用文字而缺乏“历史”的概念,对于他们来说,记忆依赖口口相传。由于难以长期保留历史,部落里的时间是循环行进的。这则小说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前文字时代记忆方式的“缺陷”,但这些记忆方式其实也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澳大利亚学者琳恩·凯利在一次对澳洲原住民祖先历史的学习过程中,意识到了这种优势。凯利发现,尽管没有文字这种可靠的记忆工具,原住民却能牢记巨量的动物信息,诸如辨识特征、行为、栖息地、习性等,他们还能很快地联想到与动物相关的大量地景的信息。凯利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当地人发明的一种叫“歌之路”的独特记忆模式:这是一种有关风景的叙事诗,原住民们将足迹所及之处的地形、景色与道路小径,吟咏成歌,让每一处意义重大的地方为人所知。在此,记忆具有了“空间性”,通过身体的操演和口语的吟诵,即便不依赖文字,这些记忆也能以一种有机的方式铭刻在他们心中。
凯利认为,当地原住民使用这些“歌之路”的方式,和古希腊的演说家有很多相似之处。演说家们同样是将记忆转化为一种空间,通过想象自己穿行于建筑和街道之间来记忆事物。这种传统甚至在现代记忆比赛冠军所用的“位置记忆法”里,依然能找到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记忆不一定意味着记录在史书上的文字,而其实是一座“宫殿”。在《记忆宫殿:在文字之前,回忆如何被塑造》中,凯利介绍了自己受到原住民的启发所作的记忆实践,并试图阐释这种记忆方式的意义。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记忆宫殿:在文字之前,回忆如何被塑造》,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记忆宫殿:在文字之前,回忆如何被塑造》, [澳]琳恩·凯利著,张馨方/唐岱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万川文化,2022年4月。
一个人到底能记得住多少事情?我现在相信了,一个记忆力正常但也会丢三落四的平凡人,只要使用专家们——原住民长老的记忆方法,照样潜力无限。记忆,是原住民保留所有文化信息的唯一方法。
我尝试模仿原住民的记忆系统,做了不下20种试验。我将不同的技术拆解重组、融汇互补,合并创造出一种几乎什么都能记忆的不可思议的妙方。我的思维越来越倚仗图像与情感,而不是文字了。这感觉非常奇特又精彩,笔墨几乎无法形容。当然,我不会因此就不努力尝试。
在想象中,我可以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而实际上,我其实只是在家里、后院与邻近社区散步。我将每个国家和所有时间都转译成符号密码,嵌置在这些空间里,每次走过我的任何一条歌之路,我都会往里面多增加一点细节。
我越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得到的乐趣就越多,而知识也就越容易牢记。接下来我所要说的记忆方法,几乎对任何主题都适用。
作为记忆空间的地景
我相信用来创造歌之路的位置记忆法,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提升记忆力的方式,而正因如此,所有无文字文化早已经使用这个方法。从原住民的地景歌谣、古希腊罗马演说家的“记忆宫殿”,到现代所有记忆冠军用来帮助记忆的“旅程”,基本上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他们在(记忆)空间里,设定了一连串真实的地点,然后将“旅程”中经过的每一个点与信息作联结。等到下次再走这旅程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想象中),只要经过那些点,就会很容易回想起相关的信息。
记忆冠军们在自己的宫殿里四处疾走,一边放入或抽取纸牌, 一边继续奔向下一个地点。原住民在朝圣时偶尔会走吟唱古道, 同时在经过周密冗长的讨论后,他们为每一处神圣地点添加纪事。在记忆旅程漫步时,通常有狗儿与我同行,在植入新信息的同时, 我也会检视早已存在的信息,我衡量着那些以往从未见过的信息联结与形态,然后再度在我想象的“旅程”里散步。
这记忆的旅程时常派得上用场,例如每次在我看电视新闻,或与来自他国的人碰面时,用的是我的“国家之旅”。我已将这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各与我熟悉的某个地点联结,这数量会随着充满活力的世界政局的变化而变动,因为这个方法非常具有弹性,要作任何变更都很容易。我从自己写作的工作室开始,然后在花园里到处晃,接着进到屋里。照着一本作者不详的古希腊教科书的建议,我把每个房间和花园各处划分成10个区。那本书的书名是《致赫伦尼之雄辩术》(Rhetorica ad Herennium),曾为希腊与罗马学校所采用,中世纪再度被发现,颇受时人推崇,甚至一直被沿用到文艺复兴时期。
在这些区之间,每到第5个地点我又以各种方式作标记(这也是希腊人的建议),在屋子里是用窗户,花园内则是以一些我能坐的东西,总之每两处标记之间一定有4个地点,这样可以确保不会遗漏任何东西。
前120个国家刚好可以放进我的花园与屋子里,其他的就摆在我每天前往面包店的路上,可能是某间屋子或商店,某条道路或某棵树。依照人口多寡来排列,中国的位置就摆在我写作的书桌后面,小小的皮特凯恩群岛(Pitcairn Islands)就放在我经过的最后一栋房子里,那里总是飘着新鲜面包的香气,好像在吸引人过去吃它。每到第5个地点,我就会加上一些助记符号,给出人口大约数量的提示,以便让我估算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
电影《记忆碎片》剧照。
大部分国家我不清楚其地理位置,因此我开始替它们编写歌谣。首先是非洲国家,我用电影《相逢圣路易》(Meet me in St. Louis)的歌曲曲调,依照地理位置来吟唱国名,走过大陆内陆各地,然后再回头经过群岛。我不知道那个旋律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浮现,但它就是这样出现了。歌谣一旦写成,就不可能在不破坏节奏的情况下添加其他新细节,所以我只能将更进一步的信息,加到代表那个国家的地点,我家或花园、房屋或店铺里。在我脑子里有一幅非洲地图,另一幅是加勒比海地区图,再后来是亚洲、太平洋……每个地区都有一首歌谣。这些地图帮助我记住歌谣,而歌谣又能帮我回想起地图,它们共同起着作用,我已分不清谁才是主导。就像澳洲原住民的绘画经常以他们的地景为主题,那图像会令人回忆起歌谣,而歌谣同时也使人记起地景和代表地景的图像。
因为太过热衷于编写新的歌谣,我忽略了知新之外必须温故,以致旧歌谣逐渐散失。于是为了让自己养成定期背诵歌谣的习惯,我效法原住民文化,开始进行周期性仪式:在淋浴时吟唱“国家之旅”,一个晚上唱一到两次;在每周一次替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遛狗时,我就唱收录在卢卡莎上的“鸟族之歌”。即使我的歌声会伤害别人的耳朵,但这几次的效果很好。我字字分明地高声唱着“我的知识”。
我在遛狗时穿越“时间”,购物或淋浴唱歌时跨越“空间”。每天,我要么回想已经嵌入的知识,要么添加一些新的东西,一点儿也不用着急,不必额外多花时间去研究,一切就这么自然地与我的日常生活相融合。如同我笔下所描述的口述文化,世俗与神圣并不是分割的两个领域,现世与神话、功利与情感,全都融为一个复杂的整体,而我非常乐在其中。
作为记忆空间的空景
所有文化,无论口述或读写,都会观看群星的结构图形,然后所有的文化都会根据这图形创造神话人物。就像西方社会熟悉的那些星群名称——猎户座、白羊座与天蝎座等,原住民也会替恒星、行星、星座,以及它们之间的暗黑空间命名,他们会记下太阳运行与月相变化的模式。对所有人类来说,天文学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科学,西方文化将相关信息储存在书本里,而原住民文化则是蕴藏在神话中。
原住民文化使用空景的方式,就和地景记忆空间一样。而星宿就是嵌置在神话里的记忆空间。相对于地景的静止不动,他们借着故事主角在空间里的来去,表现空景这种记忆空间的移动方式。动态的记忆空间,为模仿原住民记忆法增加了一个维度。空景显然可以当作日历使用,但我还是想试试别的讲述故事的办法。目前我是把物理学的故事——包括其历史和物理学这门科学本身——转译置入星座里。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对于记忆这门艺术来说,生动的故事是关键,而当我创造了故事之后,我的那些物理学家们,不再只是安静地进行研究发现:牛顿的苹果从不曾砸得如此生动,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如此激烈。在我的想象中,物理学变得非常生动逼真。然后不出所料,我发现这许多天体完美结合,形成了一个记忆空间。随着转译嵌入的知识日渐增加,地景与空景也就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我一生皆可用作学习的架构。
作为记忆空间的纸牌
当代记忆冠军之所以能记住随机洗牌后的纸牌顺序,是因为他们赋予每张纸牌一个角色,然后编写故事,将这些角色与纸牌顺序相联结。我对纸牌顺序没什么兴趣,不过我发现这个方法在某些方面模仿了原住民文化的神话人物。通常原住民都是以雕像或各种媒介的艺术形式来呈现这些人物。借由极端不同的各种故事情节,他们加入这些万神殿里的角色来帮忙加深记忆。我对普韦布洛的克奇那深深着了迷,甚至开始收集当代艺术家的克奇那创作,他们已经影响了我当下的生活,我想如果不是可携带的媒介物最能符合需求,我应该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万神殿。
我选了两副不同的纸牌来象征先人,一副是一般的纸牌,一副是塔罗牌,总共130张牌,可以代表130位先人。我挑选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依照时间先后,依序替每个人分派一张纸牌:先用一般纸牌,从古希腊作家荷马开始,到英国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接着再用塔罗牌,从法国哲学家布莱茲·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到最后一张牌,是Linux作业系统之父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
借由将传说人物与纸牌的图案数字相联结,然后我再通过传说故事来记住这些“人物纸牌”。于是当我带着狗去“时光穿越”旅途上溜达时,我的那些先人们就会在历史的正确时间点上,自己主动和物件相联结。借由纸牌与“时光穿越”之旅,我将他们按照顺序排列了起来。有时候是散步帮助我理出顺序,有时候则是在我信步绕过街角时,纸牌告诉我接下来会碰到谁。这两个系统彼此紧密配合。
既然每张牌都有了相对应的人物,于是我便开始为每位历史人物添加越来越多的细节,如出生地及家族成员、成就与奋斗、同僚和功勋等。有时说的是荒诞不经又夸张的奇幻故事,有时则直接反映现实,先人的所作所为成为纸牌里生动故事的一部分。
为了记住如此多种类型的多重信息,原住民运用了非常多的装置设备。我想试试自己的系统能否也做到这样,因此我决定在那副中世纪塔罗牌里,全都只转译收录另一种类型的信息。现在我改用塔罗牌来代表世界上78处重要的考古遗址,我以牌里的不同花色与大小“阿尔克纳”(arcana,意思是“奥秘”,大阿尔克纳简称“大牌”,指塔罗牌中倾向精神性、抽象性的22张主牌,“小牌”则指倾向具体事件或状况的另外56张牌),来代表各个区域,然后将各地理区域里的遗址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我在跟别人聊天时,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屏幕,显示着我所需要的画面,只要一想到某个遗址,纸牌便会即时提供给我相关信息。
电影《记忆碎片》剧照。
我原本就预计自己会把同副纸牌里的先人和不相干的遗址搞混,因此一开始曾试图作区分,但是后来放弃了,因为我的先人们想要参与考古学。“宝剑四”的牌上印有一个男人在岛上的图像,我设定这个男人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我的想象里,这纸牌同时也代表拉斯科洞窟(the Cave of Lascaux),因为弗洛伊德现正根据石器时代艺术家的精彩画作替他们进行心理分析。我所创造的这些故事不仅非常好记,对我来说还很有趣,我绝不会把拉斯科洞窟的画像和阿尔塔米拉洞窟(Altamira)搞混,因为也只有在拉斯科洞窟才会有弗洛伊德担任我的向导。
作为记忆空间的小型设备
被无文字文化用作记忆辅助工具的,不仅仅有天空和地景这类大型空间,还有先人画像,前一章提过的那些可携式记忆设备,也可当作小型记忆空间。我对待我这现代版记忆空间的方式,就跟地景、空景非常相似。除此之外,我还会运用触觉,去感受每一个圆珠、刻痕或打结的绳线,多增添一些其他的感觉,让当中联结的故事更容易被牢记。
目前我正利用许多木制刻件,来探索无文字文化如此广泛使用记忆板的原因。这话不是在暗示我已能掌握古代手工艺里所蕴含的奥义和精神,我不过是在体验这些工具的非凡效能,以及使用它们时我的心智运作方式,那和通过文字书写去学习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在我已渐渐相信,这套学习的方法组合在当代教育中是无价之宝。
我最喜欢的是一块卢巴族卢卡莎式的记忆板,这是一片15厘米长的木头,上面装点着带孔圆珠和贝壳。这卢卡莎的作用就像本地(维多利亚州)鸟类的野外指南。最初一看到这项任务,我发现要记住82科408种鸟类,包括它们的类别、分布地区和其他特征时,我都惊呆了。而后慢慢地,那表面看似随意排列的圆珠,在我想象中变得有次序和有结构,我不再需要带着实体的卢卡莎,因为我已对它了如指掌。
我发现要记住82科的鸟类学名非常困难,于是也像有些无文字文化那样,开始使用双关语。以“Sandpiper”(鹬科)为例,它的正式学名为“Scolopacidae”,“Sandpiper”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在沙滩派对上表演的乐团,所以这就成了我的一个故事主题,而“Scolopacidae”,发音很像“S-go-low-pass-idae”,于是我想象自己正为了参加一场派对,舞动着身体要通过凌波舞的横杆,如果身体压得不够低,就没办法过关。对于规模较为庞大的几个科,我还会添加少许的地景“旅程”。将记忆技巧交杂混合,似乎就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尽管不是刻意而为,但我编纂的故事常常带有几分道德教化的意味。我发现自己故事里的形象,虽然有着鸟类的名字,但却非常人性化,不像飞禽,这现象一直持续到我熟悉野外鸟类之后。后来这些形象逐渐变得“半人半鸟”,就像许多原住民故事里常见的人物状态一样。沼泽矶鹬(marsh)最显著的特色就在它那双异常细长的腿,于是也就有了“玛夏”(Marsha)这漂亮的长腿女孩出现。因此当我站在沙滩上时,就会知道要去寻找腿非常细长的涉水禽,以此来辨认物种。而随着我添加的细节越来越多,诸如品种鉴定、栖息地与习性等,这些故事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鹬科中有一种体形很小的成员——三趾滨鹬(sanderling)。这种体形娇小的鸟多半是在滨水地区觅食,它们会来回追逐浪潮起落,去捡拾湿地上的昆虫。然后在某天的地景旅程里,我走到分配给三趾滨鹬的那个地点时,也跟着手舞足蹈模仿起它们的动作(至少在想象中这么做了),而这段三趾滨鹬的舞蹈,让我更容易记住它们的习性。往后每次经过这个地点,我都会跳上几下。
自从学会这些拉丁科名后,我就很爱诵念,鸸鹋科(Dromaiidae)、鸭科(Anatidae)、冢雉科(Megapodiidae)、雉科(Phasianidae)与䴙䴘科(Podicipedidae)……我开始吟唱我的卢卡莎,有些歌谣中还加入鸟啼声。我的歌谣除了节奏之外,谈不上旋律优美,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些几乎没什么音乐性的短句就像音乐。当我唱到任一科时,就能“看见”这一科的鸟类身影,不再需要讲出它们的名字。因为它们不是文字,而是人物,有了这些活泼生动的影像,就足以唤起情感上的回应。
电影《记忆碎片》剧照。
我尝试凭空描摹出卢卡莎的样子,而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也观看了所有鸟儿和故事。在这张“草图”上,我潦草添加了几笔,加上羽翼的形状及鸟喙,还有我现在凭借卢卡莎想象的那些特征,然后很快我就了解到,为什么原住民制作沙画或在地上绘图,排列树叶或在树皮上刻画,结果最后反而丢弃了那些作品。因为无论在心智还是在情感上,这个描摹的过程既强大又具有成效,真正可以让这知识难以被人遗忘。
我开始为了与角色互动的乐趣而把玩故事,不再只是为了记忆知识。例如,太平洋鸥与黑背鸥极为相像,二者都是大型海鸥,这种鸥类的显著特征就在于鸟喙前端的那点红色:黑背鸥的红色在嘴尖下方,太平洋鸥则是在“鼻头”。我的海鸥故事讲的是太平洋鸥,叙述时口齿还要含混不清,就好像我喝醉酒,这醉酒正说明了太平洋鸥为什么有个红鼻子,而黑背鸥则是个健康的恶魔。这“兄弟俩”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吵得不可开交。构思他们的对话,带给了我许多乐趣。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是男人,而在海滩上,他们是鸟。这两个品种我可绝不会搞混。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不同的方法竟能如此自然地联合发挥作用,创造出了更好的记忆辅助效果,协助我牢记我的鸟类野外指南。我的卢卡莎、适合较大型鸟科的地景空间、歌谣、传说与动作,所有方法相互结合成一个极为有效的整体,大大超越了每个工具的总和。随着时间推移,我的故事神话色彩日益浓厚,但我在这方面所需要的信息也总是随时可得。我喜欢在做园艺时或睡前构思故事,有时候它们还会进到我的梦里,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并非刻意安排。我的故事很自然地越来越能让我联想起那许多我曾读过的原住民传说。
各式各样的记忆空间
毛利人有种族谱棍——旺嘎帕帕(the rākau whakapapa),我拿木头也仿着雕刻了一个。在太平洋文化中,族谱对建构知识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能对此有所理解,便有利于探索知名的复活节岛巨石像建造的原因。另外,我也选择了熟记欧洲皇室与中国王朝,借此探究不同的谱系结构。
在我的几块小型雕刻记忆板中,有一块是我根据资料中的澳洲朱林加的尺寸与刻痕而设计,用来将维多利亚灌木林中的本土植物转译收录起来。我还雕了一个小型的加缀饰木制板,这是刻意设计来代表一部内容不断扩增的歌谣集,同时也帮助我定期温习。该板大致上是依据美洲温尼贝戈族印第安人的歌谣板而做出来的。
我正在将世界艺术史转录到我个人的印加奇普里,放进那些绳结、色彩、缠绕、编辫与绳线当中。对于我想收录的信息,这项设计居然可以如此轻易便符合需求,这点让我感到惊讶。若说这项工具对于印加帝国的兴盛曾产生极大助力,我并不意外。
电影《复活节岛上失落的众神》剧照。
我也根据美洲印第安人的冬季清册,制作了一个皮革刻绘画卷,它为我的“时光穿越”之旅提供了强大支援,自1900年以来每一年都无遗漏。另外,因纽特与太平洋岛民等许多文化,都会利用翻花绳游戏来说故事,我目前也正以自制的绳圈来讲述伊索寓言。雕刻彩绘的木杆和木柱广为世界各地所采用,于是我便在工作室外的阳台上雕造一根木杆,将维多利亚州139种哺乳类动物,以及它们晦涩拗口的学名,全部依照特征和习性等分类顺序,一一转译成密码收录起来。我还将希腊万神殿和罗马众神,转译收录在6个刻成心形的木块上,每个木块各有独特的纹理。
我用来“想象”的那些方式,当中有部分是模仿波弗蒂角文化使用黏土球的方法。至于非洲约鲁巴族的16片玛瑙贝“占卜”法,我则是拿来转译收录自己花园里的植物——分装饰、食用与野草3种。在第一次抛掷贝壳时,从16种植物中选出一种,第二次抛掷时,为每种植物匹配16种属性,包括物种历史、耕种时间、开花(收成)期、播种、种植条件、病虫害以及各种变数等。
这所有实验使我相信,这些记忆设备具有不可思议的效用。在使用所有工具时,信息都会与记忆空间内的某个特定地点相联结,知识被转译收录在生动的故事里,而故事又通过想象的联结,牢牢固定在那个地点上。
我最意义非凡的一项实验是根据自己对澳洲原住民歌唱小径的认识,尽可能模仿去创造了一首歌之路。在我家附近灌木丛中的“散步小径”上,我为沿路许多“神圣地点”都取了名字,我发现在吟唱这些名称时,自己竟然能以一种从来不曾预料到的方式,去“想象”这趟旅程的每一步。我从中得到了更深入的灌木知识,那是数年来在公园中散步时从未曾有过的知识深度。借由前面所描述过的几种记忆工具,我将当中的一些歌谣与故事融会贯通,尤其是有关鸟类、哺乳类与植物等信息,每首歌谣在我的歌之路上,都有特有的衔接定点。同时我试着像许多游居文明(mobile culture)一样,依据植物的季节性开花、候鸟到来的时间,以及许多其他特征,尽可能去创造一个可以与世间所有事情相契合的历法。
我这各式各样的记忆空间大杂烩,越使用就越是轻松顺手,在创作歌谣、故事与舞蹈时都轻而易举。我的知识系统已然整合成为一个信息集合体,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毫不困难从中挑出我要的东西。如今它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在我心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如此活泼、生动而又可靠的体验认知的方式,与我之前所使用的一切是如此不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原住民文化几乎不可能解释清楚他们的知识系统,因为那就算没有几千年,至少也有数百年的经验累积。若不是实际使用这些记忆方法,我想我大概永远都无法理解。只希望能有读者和我一样,拥有完全相同的体会。
原文作者/[澳]琳恩·凯利
摘编/刘亚光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