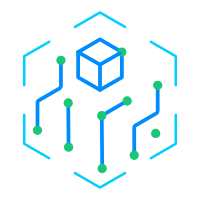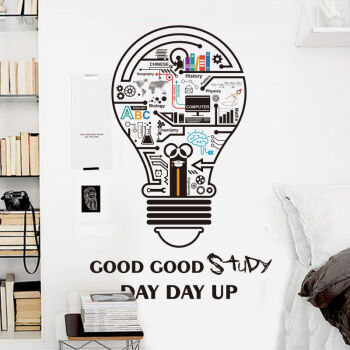解决群众诉求的措施(减少群众上访要补足)
吕梦琦
如今,为了减少上访,各地都加大投入,积极建设“雷达网”,
吕梦琦
如今,为了减少上访,各地都加大投入,积极建设“雷达网”,提升应对能力。但有的地方上访量却仍居高不下,甚至有些矛盾还激化为恶性事件。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只从结果上想办法,而不从源头上找对策。
好的经验和创新举措就摆在那里,就看基层政府能不能真正转变观念,积极去发现,发现后是不是真学、真做。
山西省交口县曾是有名的“上访大县”,高峰时每年进京上访人数高达20多批次、50余人次,年年被点名批评;但十八大以来却逐年下降,近两年降幅都达到70%,已成功“摘帽”。(详见12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
交口县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将过去每年花在信访维稳上的大量资金,用来加强便民设施,围绕“服务”创新机制,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在交口县,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便民中心、服务站等,遍布全县乡镇和村庄。基层干部作风明显好转,主动靠前服务;群众办事和反映问题“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好办了”,气自然顺了。上访量下降,水到渠成。
这充分说明,化解信访难题关键不是钱花了多少,而是钱花在了什么地方。过去,一些基层政府习惯于“截访”,习惯花钱“买平安”。一到年底,进京“截访”的基层干部就多起来。表面上看,人带回去了,矛盾也压下来了,可实际上却是“掩耳盗铃”“治标不治本”。这种人为掩盖矛盾的做法,不但形成了很多“隐患点”,也助长了政府“简单粗暴”的作风。结果,政府服务意识越来越淡薄,割裂的是党群、干群关系,留下的信访“雪球”越滚越大。
良好的服务是减少上访的“源头”。靠服务暖人心,才能给基层矛盾“釜底抽薪”。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交织,利益更加多元,环境更加复杂,国家发展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强化社会管理,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各地政府应坚决摒弃旧观念,以优质的服务带动信访机制创新,全面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各级领导干部也应该认清形势,尽快转变观念。十八大以后,过去那些“化解”信访惯用的“野路子”都行不通了。除了补足“服务之钙”外,信访工作没有别的“特效药”,再像过去那样乱作为,或者不作为、慢作为,必然被问责、拿下。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就要加大便民设施的资金投入,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尽快形成健全的政府服务体系,建成服务型政府,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困难有人管,意见有处诉。
更关键的是,各级干部要增进群众感情,增强服务意识。过去的教训告诫我们,信访矛盾积少成多、由小积大,往往与各级干部不管不问、冷漠对待紧密相关。而现实也表明,尽管不少干部“改进服务”喊得漫天响,但就是不见行动,信访工作仍以被动防、堵为主。这说明增强服务理念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需要倒逼、激励。各地应对症下药,完善制度建设,促使干部队伍不断改进作风、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激活广大干部服务群众的积极性。
■链接
从焦头烂额到交口称赞
不再花钱买平安,山西一个“上访县”是这样摘帽的
不少信访问题都是基层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小事拖大。信访成了“天下第一难”,很多领导一听信访就挠头
山西交口县将原来每年用于维稳的几千万元资金用来加强便民设施,给基层矛盾来个“釜底抽薪”
返聘“上能连通机关部门、下能连通百姓”的退休干部当乡村信访调解员,是化解基层矛盾、消解信访积案的一件“秘密武器”。用好这支力量,能“精准”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交口县双池镇调解员张保田在调解室。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谢锐佳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谢锐佳、吕梦琦
“没有服务中心调解员的帮助,我的问题不可能这么顺利就解决!”
谈起父亲被砸伤、家畜被“吓”死及房屋被震坏等问题的解决,交口县回龙乡西营塘村村民马凤鸣十分高兴,点开手机图片库向记者展示自家修缮好的新房照片。
但在2014年,马凤鸣没有高兴只有闹心。这一年,一场“飞”来的横祸让他焦头烂额。
化敌为友:一场一触即发的堵路危机化解了
引黄工程爆破“吓”死家畜、砸伤老人,村民用三轮车堵施工洞口……
2014年,山西省引黄工程下穿吕梁市交口县部分村庄,连续多天的爆破波及了住在附近的马凤鸣家。
“放炮地动山摇,像打雷一样,房顶直掉沙子!”壮硕的马凤鸣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几次爆破之后,他家房屋开始出现裂纹,成了危房。
更不幸的是,一次大爆破过后,马凤鸣的父亲被倒塌的窗框砸折了锁骨和左足,紧急送医。
不仅如此,施工爆破还造成了村子附近一口泉水出现断流,马凤鸣辛辛苦苦饲养的羊,有的被吓早产,有的踩踏致死,损失三四十只,100多箱蜜蜂也被“吓死”了大部分……
焦急万分的马凤鸣找到施工方交涉,对方答应给予解决,但就是迟迟不见行动。“扯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效果。”马凤鸣说。
情急之下,马凤鸣“采取了措施”——用三轮车堵施工洞口,造成停工。
“我那时也着急啊,父亲还躺在医院呢!”谈起当年的“过激行为”,马凤鸣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气急的马凤鸣“狮子大张口”,要求施工方赔偿200多万元。
施工方嫌要价太高不答应,马凤鸣继续堵工地不让开工。双方剑拔弩张,事情陷入了僵局。
转机在于乡里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在于返聘退休干部信访调解员。
马凤鸣考虑过打官司,但光房屋受损鉴定费就要5万多元,还有诉讼费、伤害鉴定费等。马凤鸣实在打不起也拖不起,父亲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一筹莫展的他去了水利局,又跑到县信访大厅上访。接待的同志有些“奇怪”,说这事你们乡里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就能处理,不必跑到县里。
“我当时还半信半疑,认为他们是在踢皮球。我咋不知道乡里有个什么‘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呢?”马凤鸣说。
担心被忽悠的马凤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回到了乡里。
其实,回龙乡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就坐落在集镇的“黄金地段”,马凤鸣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但平时没啥事也就“视而不见”。
整洁规范的办事大厅和亲切耐心的调解员给马凤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奔波了一两个月的他感觉到了希望。
“这的确是一块‘硬骨头’!”在回龙乡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当时接手这起纠纷的信访调解员李根保从一大叠本本中抽出关于马凤鸣纠纷的那本档案。
“马凤鸣起初要价太高,还堵了人家的工地,问题相当棘手。”李根保回忆说。
跟马凤鸣讲政策摆道理,和施工方讲利害关系,找主管单位负责人协调……李根保四处奔走,调解10多次,磨破了嘴皮,终于使“石头开花”——马凤鸣不再堵工地,施工方答应给予合理赔偿。
一颗“定时炸弹”拆除了。
翻开马凤鸣纠纷档案,里面脉络清晰地详细登记着纠纷缘由、图文证据、协调主持人、处理方法、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等。
“不打不相识”,纠纷和谐化解之后,马凤鸣居然成为施工方的“合作伙伴”,帮他们拉水,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
“这可不是我的附加条件,完全是双方自愿的!”马凤鸣特意向记者强调。
李根保告诉记者,像马凤鸣这样因引黄工程施工房屋受损的,在当地还有3个村、40多户村民,曾多次到省城上访,目前在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的调节下也全部达成协议,只等鉴定结束后进行赔偿。水利部门还安排260万元为村民打水井,资金也已到位。
“这些纠纷处理不好,就是不稳定因素,甚至发展为群体性事件!”这名拔除了大量基层纠纷“引爆点”的“资深”信访调解员说。
秘密武器:返聘退休干部当乡村信访调解员“精准”化解纠纷
退休干部上能连通机关部门,下能连通百姓,方式方法灵活,调节效果令人“意想不到”
帮马凤鸣与引黄工程施工方“化敌为友”的信访调解员李根保,是返聘干部,退休之前曾当过交口县卫生局党支部书记、回龙乡党委副书记。
聘请像李根保这样的退休干部当乡村信访调解员,是交口县化解基层矛盾、消解信访积案的一件“秘密武器”。
“还有好几面,我没挂出来。”在交口县双池镇信访调解室,记者看到墙上挂着两面锦旗,都是信访户送给被称为“民调高手”的调解员张保田的。
2014年,这名当过多年信访局长的调解员调解信访案件100余件,2015年调解70件,调解成功率和满意度都在98%以上。而今年他接到的41件信访案件,也已成功化解了36件。
本来可以和老伴在太原颐养天年,却独自一人来到偏僻乡镇发挥余热,张保田对调解基层矛盾这项工作很有感情。“当调解员要有责任心,有善心,有恒心。”有一次,为了调解一桩投诉,张保田夜宿农家,并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废矿井,终于逮住了深夜偷偷放炮的违法采矿者,成功破解了被视为“疑难杂症”的这起矛盾。“你不仅要懂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还得有根有据,人家才听你的。”这名“金牌调解员”脸上始终带着很有亲和力的笑容。
“做信访工作,特别需要上下协调能力强的人。”交口县委书记霍慧文表示,很多退休干部上能连通机关部门,下能连通百姓,处事更客观公正,身份容易得到群众认同,一般基层干部比不了。用好这支力量,既不增加人员编制,又能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精准”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一头银发的郭福海,退休前是县农业银行干部,2013年返聘回老家双池镇梁家沟村当调解员,每年都化解纠纷十几件,在村里颇有威望。
“交口县已经设立100多个乡村矛盾调解室。”交口县政法委副书记郭文海说,像李根保、张保田、郭福海这样由退休干部返聘的调解员,已经覆盖全部7个乡镇。有的在乡镇办公,有的直接进驻村里,牵头化解复杂矛盾。
“退休干部熟悉基层,威望高,方式方法灵活,调节效果令人‘意想不到’。”郭文海说。
“如果都像老李这样帮我们,谁又愿意当个上访户,时时刻刻被防着?”站在新修缮的房屋前,马凤鸣很感激关键时刻帮他一把、避免他走上过激违法邪路的调解员李根保。
变堵为疏:从疲于应付到主动服务
已经习惯于挨批评、做检查的交口县,去年第一次受到山西省信访局的表扬,并摘掉了“上访县”的帽子
返聘干部调解员李根保、张保田们能大展身手的背后,是交口县近年来摸索打造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系统。
像“回龙乡社会管理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在交口县已经覆盖了全部7个乡镇,而每个中心都有专职调解员。
“这是我们交口探索‘信访问题不出县’的一个创新。”交口县委书记霍慧文说。
除了乡镇一级平台,还有2个县级便民中心、89个农村服务站,遴选了451名网格长。每名网格长配备一部智能手机,随时上传群众诉求和各村隐患点。自2013年运行以来,这三级平台累计受理各类事件136458件,信息受理量位于全省第7,全市第1,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作用日趋明显。
“这几天有几个剪羊毛的商人在我村剪羊毛”“林业局副局长张兔旺到我村察看核桃树长势并指导村民剪核桃树”“我们有两名村民研发了一台种谷子机器”……回龙乡社管中心墙上挂有液晶大屏幕,记者看到,网格长们上传的信息及时地显示在“回龙乡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上。
县乡两级管理中心都有专人值守,随时发现各村网格长上传的各类信息,研判分析,沟通协调,解决问题。
从事信访工作的同志打趣说,以前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后来被信访取而代之了。很多领导一听信访就挠头。
而不少信访问题其实都是基层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慢慢积攒起来的。正在热映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面的女主角李雪莲持续二十几年上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部门一些官员的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最终“芝麻滚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小事件折腾成大事故”。
交口县遍布村镇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便民中心、服务站、网格长,就是为了解开这个“结”,避免“我不是潘金莲”式的上访。
端口前移,主动服务,这种变化有效“疏浚”了沟通渠道,基层纠纷一部分消灭在萌芽状态,一部分化解在村里、乡里,给信访“釜底抽薪”。
2014年以来,交口县几乎没有新增赴省进京上访案件,还去了不少“库存”,消化了不少老大难问题。2015年,交口县进京上访量更是从上年的27批次53人次下降为7批次7人次,人数下降近9成,省内上访量也明显减少。今年上半年,交口县赴省城上访量则为零;进京上访人数下降为往年的三成。已经习惯于挨批评、做检查的交口县,去年第一次受到山西省信访局的表扬,并摘掉了“上访县”的帽子。
但过去的交口,却不是这样。
交口县位于吕梁山南部,人口12万,煤、铁、铝等资源储量丰富,但由此导致的干群矛盾、村企矛盾、村矿矛盾也十分突出。“每年一到全国两会、国庆等敏感日子,县里的干部就要四处截访,有的一年时间基本都待在太原和北京。”担任交口县信访局局长近十年的梁文辉说,前些年交口县每年花在维稳上的资金少则两三千万元,多则七八千万元,但上访量却越截越多。
“过去信访量很大,为了截访我每年都要去北京两三次,很多信访人一到北京就换号了,或者不接你电话,我们只能到几个敏感的地方去碰运气,有时迎面走着就碰上了,但压力非常大,县里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情况,有时候截访的人还没回到县里,就知道自己已经被处分了。”曾多年担任交口县信访局局长的张保田说起前些年的情况直摇头。
十八大以后,花钱截访和“买平安”的办法行不通了。
交口县委书记霍慧文坦言,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不到位,群众找不到解决困难的地方,无法顺畅地表达诉求,政府总想着去堵而不是如何去“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交口县转变思路,将每年用于维稳的几千万元资金用来加强便民设施,并将政府服务性职能根据实际情况下放到乡镇和村级平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办事柜台整洁清爽,媲美银行窗口;墙上挂着的电子屏上滚动着办事流程巧用图表,明了清晰……记者在回龙乡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看到,这里不仅设有13个办事窗口,整合了计生、民政等12大类42项便民服务事项,同时还设有信访接待大厅、矛盾调节室等,极大地方便群众办事、化解纠纷。
目前,交口县已经把户籍、上学、看病、社会保障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服务事项下放到乡、村管理服务中心,很多事情群众不用到县城就能办理。
今天的主动服务,避免了往日的疲于奔命。回龙乡调解员李根保告诉记者,2015年他们一共接到80多起信访案件,基本全部被成功化解,今年已经接到的32起信访案件也已经成功化解了25件。
破解信访难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根子上解决信访这个“天下第一难”,交口县还需要解决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部分权责交叉不清、缺乏健全的担当机制等问题,这也是基层信访普遍面临的难题。
打造平安县,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