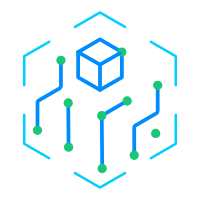山西高一心理健康教育用书(山西省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材)
可见研究口头传统有着显而易见的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旦书写文本在某个节点介入到一种文化中,口头传播的内容就有可能偶然地被写下来。书写文本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是更普遍的现象是口头文化实际上在人们的生活中(至少在古代)还是居于统治地位。透过书写文本去理解口头文本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思维的转变。那么问题就只是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这群人都精通文字和高等教育的思维体系,而令这些专业历史学家在心理上接受口头传统的重要性实际上非常难。我在另一本著作《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中已经详述过口头故事的巨大影响力,关羽的研究是另一有力例证。1983年当我还是一名在日本的留学生时,开始着手人生第一个专业研究计划,当时我就已经对中国帝国晚期的神明崇拜来源于像明代《三国演义》这种书写文本的看法抱持高度怀疑(在当时是一个被接受的学术观点)。因此我开始搜集各种关羽神祠建立和重建的日期信息。就像我在自己的书中已经详细解释的一样,如果关羽崇拜在印刷书籍的影响下不断传播,那么我们应该能找出关羽崇拜活动和神祠以文人团体为中心分布的证据——比如早期长江下游的关羽信仰应当有最庞大的文人信众——但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关羽的传说也应当与印刷出的小说相一致,但很遗憾史料上也无法支撑这一点。这些我在本书中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佛教伽蓝和道教护法出现的关帝,实际上是日渐成熟的口头传播的关羽信仰影响精英宗教的一种结果?
田海:其实这里“佛教”“道教”一类的词汇非常有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很少将他们视为独立互不相干的宗教类别。但更重要的是,我试图提出佛教与道教版本的关羽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在任何语境里,关羽的主要角色都是降妖除魔——不论是引起干旱的恶龙(这是与天台宗智顗有关的一则传说)或是在山西解州盐湖或其他任何地方引起天灾的妖魔——而这一形象的产生最初实际上和佛教道教都无关。
您在书中提到,不仅仅是佛教道教的宗教话语,连与三国时期有关的史书和文学都不是最早关公信仰的起源,反而是灵验奇迹促成了不同地区对关帝的集体崇拜。但就这一点来说似乎有些反常识,一个地区在树立某种神明信仰,并且通过宗教物体、空间和仪式具象化这种信仰的时候,难道不会从某种精英文本的原型中寻找神明身份的信息吗?或者说,是否有一套口头信仰的历史叙事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不同的信仰团体之间?
田海:很有意思,实际上你的问题应该是预设了大部分我这本书的读者脑中都会有的一种思维定式。但是为什么不识字的民众必定会从书写文本中创造自身的文化呢?这本身就是反常识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识字率极低地区的宗教文化究竟如何从书写文本中汲取灵感?我并非反对书写文本对宗教生活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但是我也认为书写文本的这种影响力是逐渐在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而且我们需要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进行谨慎的评估和研究。我们不能假定书写文本永远作为口头文化与实践的唯一来源。关羽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宗教崇拜的传播与小说、阅读文字的文化分布相迥异。相对地,我认为戏剧文化与这类信仰的传播非常相关,但是在一系列关羽戏剧中带有明显宗教标志的人物是阎王和关羽,而非关羽崇拜中的重要神明。所以我认为任何在相对偏远和低识字率的乡村进行田野考察的研究者都会强调口头文化依然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我的家族轶事,即便不是低识字率家庭,口头传播也一直是家族历史传承的主体。我的祖先十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晚明)从德国移民到荷兰,大多是法律文献的专家,在十七世纪之后的两百多年也都是荷兰比较富有的精英家庭。刚才提到的我的政治家高祖父就是法官兼法学教授,也是一所大学的校监。很明显,讲述和传承一段完全脱离文本的口头历史在所谓的“文化家庭”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作为对你和对中国读者的问题的一个回应,我只能说书写文化或许对口头文化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亟待证明(或证伪)。在此之前我们不能默认口头文化的现象一定来源于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