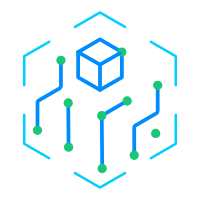大畅想艺术教育富力校区()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谈到了在新文化史的背景下俄罗斯学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而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给俄罗斯“当头棒喝”: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亨廷顿还断言,以斯拉夫和东正教为代表的文明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亨廷顿之问”的背景下,俄罗斯学者迫切需要寻找出路,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文化史复兴”和“文化学创立”的现象。所谓“文化史复兴”,是因为之前在俄国历史的宝库中有过文化史这门学科,只不过在苏联时期文化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而打压殆尽。“文化学创立”则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学”这一学科普遍出现在俄罗斯大学中,其研究的问题包括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决斗史等等。在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中也纷纷设立文化学教研室。1996年俄罗斯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的副博士学位,而2000年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伴随着文化学的出现,用文化学的理论来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学”也诞生了。“文化史复兴”与“文化学创立”是用文明史观的理论来反击亨廷顿,因为俄罗斯学者认为,亨廷顿不过是借鉴了汤因比的理论,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理论源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而后者的理论则可能继承了达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观。
俄罗斯学界在新文化史转向后发表了许多成果,张建华教授推荐了3本当今俄罗斯的文化史和文化学方面的代表著作:沙波瓦洛夫(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Шаповалов)的《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康达科夫(Игорь Вадимович Кондаков)的《文化学:俄罗斯文化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和谢缅尼科娃(Любовь Ивановна Семенникова)的《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除此之外,还有一本“极端”的成果——安东·乌特金(Ан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ткин)的《环舞》。乌特金是作家、导演,获得了2004年的“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而其小说《环舞》获得了2015年“全俄历史学和社会学奖”。虽然乌特金的职业与历史学看似无关,但他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文献学教研室。2016年乌特金携其《环舞》来到中国参加读者见面会,谈到历史学专业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乌特金认为这个专业使自己有机会阅读和研究一些常人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史料,这对于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很有帮助。以《环舞》为例,小说讲述了19世纪俄罗斯青年军官的故事,他曾参加许多历史活动,包括镇压高加索、波兰的反俄起义,书中谈及了他对文化的感受。这是新文化史背景下当代俄罗斯史学的一个变化,而且此类变化在中国也发生了。比如,王笛的《袍哥》就获得了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其获奖词中写道:“……是考察历史与叙事、文学与史学关系的绝佳例子,是当代史学致敬本土史传统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就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接下来张建华教授介绍了在新文化史的冲击下欧美学界俄国史研究中发生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后,欧美学界对“预测不准”的重大失误展开反思,因为苏联解体是以一种“突然死亡”的特殊方式出现的。1991年12月8日,3位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突然发起“苏联解体”的倡议,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停止存在。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苏联是一个核大国,核武器广泛分布在其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中,如果苏联发生内战,就可能殃及整个世界。西方的战略家、国际问题专家们对“测不准”的错误纷纷自责,他们的反思结果是,以前的“苏维埃学”过于单一、功利、模型化,因此要“超越苏维埃学”。莫蒂尔(Alexander Motyl)在其《苏维埃学、理性、民族性:论苏联的民族主义》(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中强调,要研究苏联的民族主义,必须从其“民族性”着手。欧美学界反思,以往单从线性的、理性的、实例的角度研究苏联历史是不够的,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国际研究。“国际研究转向”因此出现,在此背景下诞生了诸如《俄罗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