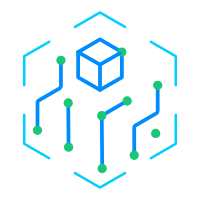大畅想艺术教育富力校区()
张建华教授还分享了自己2016年6月2日至4日在慕尼黑大学参加为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的经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俄国革命文化及其在全球的影响:语义-表现-作用”(The Cul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Global Impact: Semantics – Performances – Functions),他所在小组主要谈论了十月革命在东方的影响。此次会议的发言反映了在史学新潮流背景下欧美学界的变化,比如马丁·奥斯特(Martin Aust)做了题为《俄国革命的全球化:一些史学评论》(“Globaliz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me Remarks on Historiography”)的报告;张建华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北京“老莫餐厅”的记忆: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化在当代中国形象的变迁》(“The Memory of Restaurant Moscow in Bejing: the Changes of Image of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ovie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报告。
如何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
李剑鸣教授2012年在《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中曾写道:“……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国内学术界谈论这个话题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些说法还没有过时,虽然中国学界了解新文化史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海登·怀特在内的新文化史大家也曾应邀前来中国,但是有影响的著作还是寥寥无几。对于这样的现象,张建华教授借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话题“谁之罪”与“怎么办”进行了发问,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以中国历史为基础,借鉴“他山之石”,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张建华教授曾就这个问题发表题为《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的文章并在其中指出,建立中国的“俄罗斯学”学科是可行的,它应当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开放型的、宏观视野的学科,它应该是一个以文明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用来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张建华教授认为可以以中国史学传统,即“义理”、“辞章”、“考据”之学为基础,借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经世致用”、“秉笔直书”等史德,用它进行指导,再吸收国际史学界最新的成就,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学科。
第二,从你我做起,人人都是史学潮流观察家,人人都做历史理论家。刚才谈到,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起初在俄国乃至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历史学不单独设系,而往往是历史语言系或历史哲学系的组成部分。1934年在苏联才出现了独立的历史系,与哲学系、语言学系分家。从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以来,历史和哲学、语言一直是合二为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学习历史的学生不仅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历史事件的年代,还要知道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他们接收了完整的人文知识教育。现在的欧美国家还有古典系,是“打通文史哲”的大学科。张建华教授认为,恰恰是由于巴赫金和雅各布森在大学阶段接受了这种“打通式”的专业教育,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出被不同学科采纳的观点。以赛亚·伯林虽然在1918年就流亡英国,并没有在俄国读大学,但是他曾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相似的还有科耶夫,他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还是欧共体的主要创建者和欧元的主要设计者。他出身于莫斯科的富商家庭,其叔叔是俄国画家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ндинский)。十月革命后,还是中学生的科耶夫曾因倒卖粮食被捕,之后他越狱,并于1919年离开苏俄,前往德国。之后他在德国经商,并在莱比锡大学旁听。他雇哲学家到自己家中授课,其中包括雅斯贝尔斯,后者成为了他的博士生导师。毕业之后科耶夫前往法国,由于没有国籍,他不能在大学担任教职。不过他从1933年到1939年曾在讲习班中讲授精神现象学,而他的听众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拉康、雷蒙·阿隆等人。也有一些人没有亲自听科耶夫的讲座,而是间接接触了他的思想,比如萨特和弗朗西斯·福山,后者的“历史终结论”可能与科耶夫“历史终结”的观点有关。1939年科耶夫获得法国国籍,他在战后放弃研究投身政治,成为法国驻欧共体代表,可谓一位“奇才”。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都在俄国接受过中学教育。在帝俄时代,俄国有三类中学:在面向大众的中学(школа)中进行基础教育;在文理中学(гимназия)中主要学习语言学、演讲、修辞等人文知识,在这里只有上层子弟学习;此外还有贵族学校(лицей),这类学校也只对贵族开放,讲授人文知识。以赛亚·柏林和科耶夫就曾在这些上层的中学就读,所以他们尽管没有在俄国的历史哲学系接受学术训练,但在其中学时代已经在历史、语言、哲学等方面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张建华教授认为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教育促使一些学者成为了新文化史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