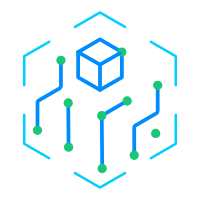义务教育阶段免书本费吗(义务教育阶段书本费免费吗)
借,还是不借,是个难以选择的问题,想起来就让人头疼。而关于“借书”为啥能引发那么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书人的种种“恶行”。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
从借书手抄的书生,到慷慨实践“共书”精神的藏书家,古今中外关于“借书”的故事,背后也总蕴藏着当时的人们对书籍、阅读的不同态度。今天的文章爬梳了许多关于“借书”的历史趣闻,透过这些旧日的读书轶事,作者也在观察着当下阅读的变化。
撰文|王宏超
借还是不借,
这是个问题
有客人参观藏书家的书房,问道:“您可愿意出借藏书?”“绝不,只有傻瓜才会借书给别人。”他扬手指了指偌大的藏书室,补充说:
这里头所有的书,全是从一群傻瓜那儿借来的。
([美]汤姆·拉伯著,陈建铭译:《嗜书瘾君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被人借书,对藏书家来说向来都是个要命的问题。道德家有言在先:“不为人所忠实地归还的东西,无如书籍。”(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借,还是不借,如同生存与毁灭,想起来就让人头疼。
古人得书不易,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担,所以借书而读是常事。为了能在归还后还能有翻阅之便,穷书生们得书后往往是边读边抄,欧阳修幼时家贫无资,“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忆苦思甜,遥想自己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真是励志的好故事。
寒门士子借书而读,终而成才,史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成名后他们有时也会记得借书的情谊,力尽所能再助益他人。后蜀名臣毋昭裔早年借书遭遇白眼,发达后立志刻板印书,惠及一时学子并两蜀文风: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
明清出版业发达,书价虽有所下降,但要遍读典籍,靠自己购置也非易事。坐拥书城,尽兴饱读,想必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黄侃先生学问好,嗜书如命,“有余财,必以购书”(章太炎语),但所需之书亦不能全靠购得,借书在所难免,他曾感叹:“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此“何年”之叹,恐怕要一直叹下去,生命和钱财都有尽,而书海却无穷。

钱钟英:《向友借书启》,《桃坞》,1927年第10卷第1期。
借书者还有一种心理,“书非借不能读也”,此说出自袁枚,他透析此类人的心理,颇为微妙:
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袁枚《黄生借书说》)

《张生借书》,《启蒙画报》,1903年第2期。
用借书督促看书,坊间流传最广的例子是钱锺书先生,据说钱先生并无多少藏书,看书都是去借。这一说法看似有理,细想无理,深思一下简直就是胡说。看书主要靠内在的兴趣驱动,定时还书的督促大半是没用的。钱锺书先生定是无须通过还书的紧迫感来督促读书。而且,匆匆阅读,囫囵吞枣,效果可想而知,梁鼎芬的《丰湖藏书四约》就明言:
凡借书不得过三种(种数过多,难于查检,且贪多则不实,好博则不专,非读书有得之道)。
藏书人的“抠门”
借书其实还附带有许多社交的功能。借书在过去也常是老友之间串门的由头。令狐揆卜筑涢溪之南,雪夜跨马去老友张君房家里借书,“一童子携琴囊书簏随之,因得句曰:‘借书离近郭,冒雪渡寒溪’。林逸绘以为图,可称韵事。”(严羽《柳亭诗话》)颇有点像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意味,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