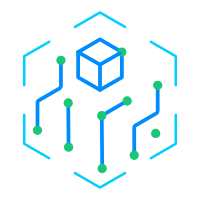周口众优教育具体位置(周口众优教育地址)
说者言之凿凿,闻者亦多信以为真。可这样的认识真那么合理可信么?
如前所述,关于这位帝尧,传世文献中最显切实、也最为原始的记载,不是《尚书》,就是《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尧的记述,就是本自这些文献,而这也是后世谈史论史者直至当今学人所能了解到的对帝尧生平事迹最全面、最系统、也最权威的记载。
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尧,或者说这一帝君的原型,终究无法知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今天能够努力阐明的,只是他在古史传说中的基本情况。不管帝尧其人以及所谓尧都是不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真事儿,古今学者在论述尧的活动地域和尧都问题时,理应以上述内容作为基本依据,现代考古学家也不例外。不然的话,这话就无从谈起——即论者若是在此之外别采他说,你又根据什么能够轻易排除《尚书》以至《史记》的相关记载呢?至少我在这里论述尧都问题,是没有缘由能够径自抛开《尚书》以至《史记》的记载而另辟蹊径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审视汉碑当中与尧都相关的铭文,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谈到以古代石刻铭文治史,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在内,很多人一下子就会想到新发现、新出土的碑石或是墓志。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圈内就弥漫着高度仰赖新材料、竞相争抢新材料的风气,甚至非“新”不成文,无“新”不论事儿(实在找不到新材料,你也得从太平洋彼岸踅摸一套“新方法”)。要是没有新材料,你就是写了、论了,人家也不屑于看。可在我看来,正常的历史研究绝不应该是这样,醇正合理的石刻文献利用形式也不会是这样。
伴随着金石学研究在北宋中期以后的兴起和发展,汉碑铭文早已成为传世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北宋中期欧阳修撰著的《集古录》和北宋末年赵明诚撰著的《金石录》,由于碑刻研究还刚刚起步未久,两书的著录都很不全面,研究的深度更相当有限。至南宋学者洪适撰著《隶释》和《隶续》,才开始系统、规范地著录碑刻,也把碑刻研究推向深入(事实上这种变化同两宋之间史学研究风气的变化是同步的,即进入南宋时期以后,史学研究特别注重对具体史事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追求)。洪适这两部书,也成为传世石刻文献中的高水平代表性著述。尽管继此之后还有不少汉碑的发现、著录和研究,但对于我来说,直至今天,洪适这两部著述仍然是利用汉碑治史的首选书籍。
稍习两汉历史研究状况的朋友都应该能够知道,相对于西汉,东汉的研究状况一直要相对清寂很多,也要相对滞后很多。其中一项重要体现,就是对汉碑的利用大大不足,而在材料来源方面,就连《隶释》和《隶续》所著录的碑文都鲜少被认识,被利用。这是很不合理的,也是很不可思议的。
下面,我就主要借助《隶释》著录的几通汉碑,谈谈我对尧都问题的认识。
《隶释》开篇展现的第一通石碑,题作《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这通碑文,更早著录于欧阳修的《集古录》,惟题作《后汉尧祠祈雨碑》(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这两种著录形式的差异,是一称“尧庙”,一作“尧祠”。不过稍习汉碑者都不难看出,这两种碑题,不管哪一种,都不会是碑石上固有的篇题。据碑文,此碑在东汉济阴郡成阳县。《隶释》中接下来著录的第二通石碑《帝尧碑》,同在成阳,应与前碑同立于一处,而碑文内有“造立灵庙”和“即尧陵庙”的语句,因知二碑应立于尧庙而非尧祠。虽“祠”字亦有“庙”义,这通碑文里也有“大祠”的说法,但在这里,考虑到帝尧的身份,还是应当以“庙”为正,欧阳修《集古录》“尧祠”的题法不够确切。

清同治十年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
关于碑文叙事的主旨,也就是竖立这方石碑的用意,究竟是记述修造尧庙的事功,还是载录在尧庙祈雨的效验?在我看来,应是前者,即欧阳修《集古录》拟定的篇题也不妥当,还是《隶释》的题名更为准确。
此碑上石于汉桓帝永康元年修治尧庙完工之际,而其具体月日久已泐损不存。不过桓帝在延熹十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康(《后汉书·桓帝纪》),故延熹十年与永康元年实际上是同一个年份(即前半年是延熹十年,后半年更为永康元年),其刻碑立石,自在这一年六月庚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