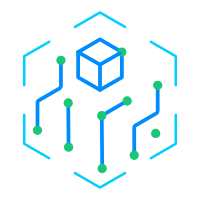古代教育文献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献)
见于《急就章》上面的文字,是行政、司法中使用的极为特殊的专门用语,而且在学童几乎无缘的边境烽燧出土了大量练习废弃的实物。由此看来,需要《急就篇》的是勤于烽燧的吏役和士兵,《急就篇》《苍颉篇》等字书,更可能是书写行政和司法文书的人们的参考书。书记官未必全是谙熟文字的老手,资历尚浅的新人还必须学习必要的字句,《急就篇》和《苍颉篇》就是这方面的字书。[5]
可见《急就篇》的全部内容都涉及吏事,是从学习为吏的角度编写的。有人认为:“《说文解字》之前,所有字书都是蒙学读物,或曾用作蒙学教材。”[6]但《急就章》用作蒙学教材,针对的是汉代学吏这一群体,有非常具体指向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可以视为学吏者的专用教科书,与后代学童启蒙教育所用的蒙学读物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急就篇》“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亦非蒙求诸书所可及”,隐约指出了《急就篇》并非一般普通儿童启蒙学书教材。现代亦有学者指出,《急就篇》“为当时学吏者学书、识名物所使用的课本,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7]。启功在《〈急就章〉传本考》中亦说:“惟苍颉正字,当非简堕之体,而纵任奔逸,岂可以教童蒙。且篇中明言‘用日约少诚快意’,可见急就之义,犹言今日速成。颜注学童急当就此奇好之瓠,及晁氏所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诸说,尚失命篇之旨,况指为书写之迅疾乎?此情理之未安者。”[8]是知《急就篇》之为名,原取学吏速成课本之意,后世视之以一般童蒙学书教材或缓急可查的字书,应该都不是《急就篇》成书的本来目的。

20世纪西汉简牍的发掘,为我们了解汉代宦学文吏学书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实证。1977年8月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有《苍颉篇》三简、疑为《苍颉篇》等字书三简,有《甲子表》练字书一简。过去在敦煌、居延等屯戍遗址也有《苍颉篇》《急就篇》等汉代流行的小学字书简牍出土,但未明言是何人的习作。这次出土的烽燧竹简却不同,考释指出:“塞上吏员缺乏,多于士卒能讽书习字者中培养擢选,故上述烽燧遗址中经常出土《苍》《急》等小学书以及吏士们练习的杂书简。”[9]这一论断与古籍记载相印证,也符合烽燧之地的历史实际,是可信的。烽燧竹简的内容多名物、姓氏,正是吏士书写公文时需要使用的常用字。
因此,从《急就篇》的内容和特点看,汉代字书是汉代宦学文吏的专业教材,并非一般社会儿童的启蒙文字书写识读教材。然而,我们说《急就篇》是汉代文吏学习文字书写的专用教材,并不否定此书亦曾作为当时普通幼童的启蒙学书教材。顾炎武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10]这确是事实。《急就篇》由宦学教材转为蒙学教材,实与汉代宦学的兴盛有极大关系。汉代教育,有经学、宦学,当时儒生也弃经典而“随时变化,学知吏事”,“踵文吏之后”,“昼夜学问,无所羞耻,期于成能名文”。[11]看来宦学比经学更昌盛,有更强的吸引力。汉代宦学,虽然不属于蒙学教育,但是,它受“讽书”取士用人政策制约,教育与利禄挂钩,势必影响蒙学教育的认字教学、讽诵教学和写字教学,势必引导蒙学向只重视书面语言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礼记正义:卷一 曲礼[M].郑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231.
[2]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 程材[M].北京:中华书局,1990:539-540.
[3]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 程材[M].北京:中华书局,1990:543.
[4]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 程材[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2.
[5]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M].富谷至,刘恒武,译.黄留珠,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2.
[6]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31.
[7]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J].文史哲,1984(1).
[8]启功.急就章传本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
[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汉简研究文集[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23.
[10]顾炎武.日知录外七种:卷二十一[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二 程材[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