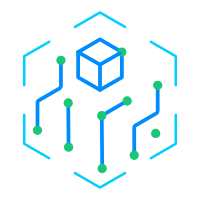程志强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年论文答辩会合影:答辩委员左起戴鞍钢老师、杨国强老师、江晓原老师和周振鹤老师。沈渭滨老师也是答辩委员,当天因为突然生病未能前来,由戴鞍钢老师代为宣读意见。李世众兄是答辩秘书。
王老师因其视野的宽广与思考的深度,对我的研究总能给予提升高度的指导。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他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一对关系,在中国近代明确提出来,到目前为止,我看出来还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交融问题。……还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探讨。这样,这个课题本身研究的延长线很长,不是把资料做完就完了。这个延长线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帮助的。”思考科学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关系与演化、寻求科学与人文交融途径,是我未来学术道路上一个高悬的目标。
除理论思考与辩证思维之外,王老师对我行文中的用词准确性与简洁性也有极大的帮助。刚到所里那几年,因为各种任务较多,逐渐被归入“快手”行列,自己虽有所醒悟,但一时间还找不到“抓手”。后来与李世众兄等一起随王老师编撰华东师大版全国中学历史教材,王老师对每句话的精雕细琢,对每个用词的反复推敲,对冗词的坚决删除,对我在逻辑、修辞、语法与语境上都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11月3日,王老师在发言中还说:“我今天来还有一个意思,代表张剑的老师沈渭滨。……我想,如果渭滨今天在的话,他的高兴劲可别提了,一定是手舞足蹈,因为他是表现型的。”沈老师和王老师是我学术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上课都非常好,激情洋溢,引人入胜,学生们时时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知。如果有排名的话,沈老师上课在复旦历史系名列前茅,王老师在华师大历史系也不居人后。第二,嫉恶如仇。常常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对学术界的不公与不平总是“拔刀相助”,极力维护学术规范与学术尊严。对抄袭者的痛恨有时会延伸到导师,指责他们的失职与失责;对导师在学生论文署名甚至完全窃取学生成果也同样深恶痛绝。第三,都具有元气磅礴的生命力与积极乐观的生命意识。两人因病都有脚疾,不良于行,沈老师晚年以文明棍助行,仍然腰杆挺拔,不要人搀扶;王老师更是借助“宝马”走四方,观风察俗。他俩因研究方向不同,专业的学术讨论会上很难聚在一起,但上海本地的不少学术活动上常常见面。在会场,他们往往因观点犀利或论辩出彩成为会议的焦点,两人有时也会互相论争,打打嘴仗,但多数是声气相通。

王老师与沈老师在历史所一次学术会议后饭桌上的交谈。
当年沈老师住院后,王老师急于了解沈老师的具体病情。我告知沈老师因过去患血吸虫病留下病灶引发弥漫性肝癌,王老师说希望沈老师不要遭受痛苦,因为肝病疼痛难忍众所周知。上帝保佑,沈老师没有遭受这个劫难。沈老师去世后,王老师亲率程念祺老师、周武兄等众弟子到沈老师七宝家拜祭,并说:“渭滨,天堂好啊,天堂清静,你可以好好写你没写完的书了!”后来,王老师撰文《最后的乡绅》纪念沈老师,说“渭滨长我一岁,向以兄长视之。虽平日往来甚稀,但惺惺相惜,心灵间的沟通有如神助,向无障碍”。回忆同作为“陈门弟子”的相知相映,说陈先生去世不到30年:
经岁月的洗涤,有立马变脸批判先生学术的,有后来不爱惜同门情义自取其辱的,也有逐渐疏离先师宗旨曲学阿世的,乃千古如此,殊不足怪。但自称私淑弟子的渭滨,一直奉先生为再生父母,凡有关维护门风师教的,他都容不得半点沙子;见猥琐诟秽,则拍案而起,敢怒敢言,有甚于嫡传弟子,由此我对渭滨也就格外地敬重。
沈老师生于七宝镇,终老于七宝镇,对七宝的文化建设尽心尽力,被王老师誉为“最后的乡绅”。王老师何尝不是如此,对他的家乡江南小镇——昆山陈墓即今天的锦溪,一样的梦牵魂绕!

王老师在2019年11月3日会上发言:这是王老师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出版社摄有高清录像,留给我们无尽的想念。
对自己所患病疾,王老师很是坦然,对科学更充满了信心。11月3日的讲话中,他曾说住华山医院一年半的体念,“我告诉各位,过去我们对癌症的可怕性现在完全不必要了,癌症一点也不可怕,而且现在癌症化疗也没有多大副作用。”并开玩笑说:“当然,也有缺点,癌症这顶帽子戴上后需要长期治疗,所以它跟右派帽子不一样,不能改正与脱帽。”他病情稳定,我们都很高兴,以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春节还未开始,疫情突然爆发,不能正常去医院探望他。虽然挂念但想病情稳定,疫情总有消停的时候。不想,五一前后病情急转直下,经预约带着沈老师新出文集《士与大变动时代》去看他时,已经不能很好地坐着说话,急忙找护工一同扶他上床平躺。他对我和随后来探望的阿明说,“已经转移到肺部,抽烟使肺部成为最为薄弱的部位,抽烟还是有害的。”开始以为沈老师的书是我的,要我签名,拿起来一看是沈老师的,他就笑了。最近一再观看11月3日的会议录像,他进门时中气十足的爽朗笑声,讲话时的神态与语态,再也不能见其人、闻其声,聆听其教诲,不仅悲从中来,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