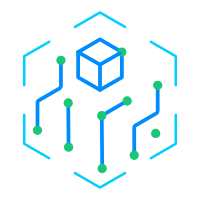云南教育云中心是干嘛用的(云南教育云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虽然任一观念都有其现实基础,但如前所述,人不一定能或者永远无法全然察觉这些因素,因此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一个至臻完善的地步,达到一种绝对正确。正是这种意义上,阿尔都塞说人们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但同样是历史性使得这一结论不那么消极。在齐泽克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阐释中,“绝对知识”并非历史终结。相反,我们无法把握绝对,恰恰是因为我们反复为自己设立这样一个不可能的目标。齐泽克认为,绝对无非是有限规定的自我扬弃,是绝对反思本身。从而对康德的回答或许是,你说得对,人达不到彻底笔直,但是那又怎样呢?我们不需要绝对笔直,只需不断超越当下。
近日一位哲学系同学和我谈起心中的失落,因为感到理论中描绘的理想与目睹的现实产生了巨大落差。但我想这种失望也蕴含着改变的动力。如马克思所言,必须做的事情,就必定会实现。或许现实真正无情的一面是,为了解决面前的问题,我们并非无能为力,相反必须不停地有所作为。即使人不愿面对现实,现实也将强迫人正视它。当前人们在以自己的行动应对疫情,日后还会有更多的挑战。世间或许无所谓完美,这太好了,倘若有一天所有人必须停下脚步,不是更加可怕么?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双重的意义上,永远坚持自己的否定性,改变那雕刻了我们性格的凿子,同时改变我们自身。我想疫情所教给我们的一点即是,人并非宇宙的灵长,并非万能,甚至其实很脆弱,但认清这点以后我们依旧要对未来保持信心,要相信自身的力量,因为除此之外无可信赖。
马彬:陆老师选的这个话题,我最早是在伯林的书中看到的,“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是伯林经常引用的一句话,甚至伯林的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扭曲的人性之材》,而康德的原话是出现在他的历史哲学著作《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之中。
让我们来简单概括下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基于“自然不做无用功”这一命题,回应了人类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制度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康德明确地指出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本能的会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但是同时也有一种要求自己单独化或孤立化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对抗性”。康德在其中举了一个例子来阐释对抗性这个概念,森林里的树木由于为了获得生长,需要相互竞争,逼迫双方互相超越对方,从而“获得美丽挺直的姿态”,但是在旷野中自由生长的树木则任意伸展自己的枝叶,因而歪歪扭扭。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对抗性推动着人类向前发展。
但是这种对抗性是基于一种“历史的合力”,是人类作为整体发展的结果。对于个人来说,康德则断定“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康德在此认定个人不可能完成那种理想的终极目标,而唯有在整体的对抗中完成。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康德会说“为一民族立法,并不需要有一群天使般的人民才可以,哪怕有一群魔鬼也可以。”或许不同于卢梭,在他看来只是拥有完美的法并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培养出“天使”般的人才行。这样我们的问题“曲木之材,何以求直”的问题就转化成了人是否内在的具有完美的可能性。
康德与卢梭诉诸于两种不同的路径来为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而努力,但是二者很明显的在同一目标下,对人性的定义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于人是否能够完美。在谈论人内在方面是否具有完美性可能之前,我们还应先讨论下对我们起塑造作用的环境。在关于人性塑造方面,我更赞同卢梭的观点,即“没有哪一国的人民不是他们政府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在18世纪,卢梭下此论断是为了强调一个契约下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人的巨大影响,当然他是在针对他那个时代进行书写的。
而现代,塑造我们的更多的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部分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应对,就像是搭乘一个汽车并不意味着我需要懂得它的所有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上网但不必了解网络的运作方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下,大多数人们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韦伯却警惕的发现,虽然我们人类的科学进步了,生活更便利了,有了更多的享乐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与人的交往变少了,时常感到被束缚,也更容易焦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