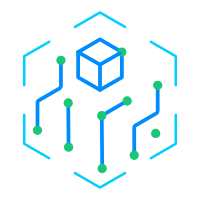陕西民间艺术教育随笔(陕西 民间艺术)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的疑惑是,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中国人习惯于利用神,他们的信仰在功利性面前随时都会崩盘。但是其他人群呢?他们难道对神只有尊重而没有利用吗?《金枝》一书告诉我们,在人类的野蛮时期,人和神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有的特殊的人是被当做神来看的。但是他们对这些神的态度其实也是幽昧不清的。“柬埔寨的火王和水王是不允许自然死去的。因为他们中谁若患上重病,长老们认为他无法康复,就会将它刺死。刚果人相信,如果他们的大祭司自然死去,世界就要毁灭。因此当他生病很可能会死时,他的继承人就会带一根绳子或棍子到他房内,将他勒死或打死。”为什么要这么血腥暴力?因为只有如此,“人神”的灵魂才能传给下一个精力旺盛的人。这哪有什么神性的存在,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而已。所有这些,不管是带有多少巫术的成分,无不是为了人的实际利益服务。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反观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实用理性的民族思维模式,好像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反倒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误解。既然其他民族也均有这个特性,怎么它就成为我们民族固有的标签呢?这也许是《剪纸》一书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向度。
说到剪纸的艺术性,正如张志春所言,它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符号的艺术。“图像的能指与所指是人为的主观性建构,而并非必然的客观性链接。”这深刻地揭示了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品种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剪纸的内容和意义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比如蛇盘兔不意味着弱肉强食的恐怖,鱼戏莲不意味着自然环境的优美,抽烟和对烟不意味着对烟民动作的写实性描摹,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对于富裕生活的追求,对于男欢女爱的渴望和对于传宗接代的精神诉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毫无逻辑的关系。但是中国人看到这些图符就会有心照不宣的心理认同。因此,如果不从符号的角度来理解剪纸,就永远看不懂剪纸。正如张志春所言,这种程式化的能指和所指往往是固定不变的。追根溯源,只能说这种特有的思维习惯来自遥远的古代,应该还是泰勒所说的幸存。
实际上不仅仅是剪纸,刺绣、布堆画、熏画等众多民间艺术,中国建筑的木雕和石雕艺术都具有和剪纸相同的符号式的思维模式,都会用固定的图符表达固定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诉求。比如蝙蝠寓意幸福,桃子寓意长寿,牡丹寓意富贵,鸳鸯、并蒂莲代表夫妻恩爱,百合、核桃代表百年好合,石榴、莲蓬代表子孙兴旺等等。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形成了民族的长期的文化积淀,可见,不了解文化特性,也就不了解艺术特性。这种思维惯性也浸透到中国的国画当中,比如,表现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画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特别的、固定的寓意。
人们对剪纸艺术性的感受还在于它的多视角、多向度、多时空的表现手法。正如书中所说:“作者的目光好像全能叙述者的目光、神灵的目光一样,穿透一切空间建构,超越现实中的障碍,至于在一个空间里,时间可以浓缩状态呈现,譬如不同时间的花卉荷菊梅兰同时绽放,或同一枝杆上舒展不同的花叶,结出不同品种的果实;甚至一个事件不同时段的情节比并而出,瞬间爆场,在剪纸世界中更是司空见惯。”这种论述准确地概括了剪纸艺术性的一个本质特征,我将其概括为“全视角构图,全时间叙述”。每一个剪纸艺术家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好像都成了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能从一个物体的正面看到侧面和背面,从表面看到内部,从此时看到彼时,从现在看到未来。甚至她们都是一个个无所不能的神,可以对人间事项、现实物体任意安排和调度,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任意调序和穿越,只要是符合她们的主观意愿即可。所以剪纸表象是唯物的,本质是唯心的。剪纸就是典型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艺术实践活动。
人们总习惯于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剪纸进行对比,这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但是这种对比的目的是以现代艺术的高大上来烘托剪纸的文化价值,这在发掘和普及剪纸知识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实际上是缺少自信的表现。西方的现代艺术是在曾经辉煌的写实传统基础上求新求变的结果,而中国的剪纸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说,是西方的现代艺术靠近了中国的剪纸,而非中国的剪纸靠近了西方的现代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某剪纸艺人是中国的毕加索,不如说毕加索是中国的某剪纸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