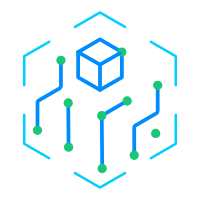幼儿思想教育工作规范管理计划(幼儿园思想教育工作计划)
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号召男女平等,提出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理念。运动主张女性掌握自己的身体和生育,在政治实践中要求生育权、堕胎权和健康权,其中堕胎合法化的要求成为女权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女权主义者的这些理念和政治诉求,直接冲击着坚守性别差异和男女有别的宗教自然法则,威胁了美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中女性服务家庭、臣服于丈夫的理想性别模板。这些自然也被保守主义者认为是道德沦丧、威胁神圣家庭秩序、背叛上帝意志的倒行逆施。
实际上,追求平等和解放的女性运动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反女权运动的阴影。在18世纪初19世纪末的第一次女权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争取和男人一样拥有投票权,反女权运动已经就女性参政的问题上提出“反妇女选举权”的意见,并且形成了例如反对妇女投票权的全国协会(NAOWS)这样的组织,进行游说、演说等各种活动。这些组织和其成员认为男人可以代表女性的政治意愿投票,女性应该恪守家庭,而不是歇斯底里地参加抗议或选举活动。20世纪60和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里,当美国女权主义者们发展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理论,挑战公私领域的分界线,试图开展以个人生活和家庭领域为斗争中心的政治运动时,持反对意见的妇女认为家庭才是社会的根基,相夫教子才是女人的目标,妇女在家庭中才能保持个人尊严。当女权主义者编写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来论述堕胎权对女性的意义,要求女性获得对身体的自主权时,反对的声音认为堕胎就是谋杀新生命,堕胎是逃避女性天然的生育责任,“堕胎良心要受到谴责”。
在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对堕胎的道德看法发生松动,部分州开始修改法律赋予女性一定的堕胎权。1973年“罗伊案”标志着女权主义者在堕胎权运动的政治成功,但它也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更深远的连锁反应。此判决一出,围绕堕胎的矛盾激化,拉开了 “选择权”(pro-choice)和“生命权”(pro-life)正反两派争锋拉锯的帷幕。更重要的是,不同宗教团体、保守右翼势力和反女权运动在反堕胎问题上达成一致,“罗伊案”自身的法律漏洞和当时女权主义运动存在白人中产女性中心视角,忽略了有色族裔和工人妇女等群体的诸多缺陷,使它成为一个靶子。反女权运动、保守宗教势力和“新右翼”政治势力借此结合,原本零散的反对势力就此团结统一起来,形成同一阵营。
我们很难直接说“罗伊案”成为了1970-80年代女权运动遭到反女权运动回击的转折点,但从时间上看,这与女权运动在美国当时的社会走向衰落是大致吻合的。1970年代后期,反堕胎队伍不断壮大,并且在实践中充分利用代议制政治规则,在竞选中抵制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候选人,把堕胎问题变成美国两党竞争时难以回避的问题。激进的反堕胎人士甚至炸毁实施堕胎的诊所,对堕胎妇女进行人身攻击。各种反堕胎委员会或者组织持续不断地尝试推翻“罗伊案”,或者在现有框架下,在州一级的法律和行政中寻找限制妇女堕胎的可能。1976年,海德修正案通过。该措施禁止将政府资金用于堕胎服务,除非是强奸、乱伦等情况,此后一年,美国一半的州调整了医疗服务政策,对堕胎者进行严格限制。有学者认为,整个70年代后期,堕胎权非但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在攻击中丧失阵地。而反女权运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司法运作,则让堕胎问题不仅限于家庭和女性的个人私生活,“进而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妇女运动完全陷入困境。”
不得不提的是,反女权运动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堕胎权。早在1923年,美国“全国妇女党”起草制定了《平等权利修正案》(ERA),试图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彻底消除各个社会层面对女性的歧视,从而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而1970年代的反女权力量也把阻止该法案的批准看做是使命。此后,这部意在让美国宪法承认性别平等的草案也未能争取到美国四分之三的州,即38个州的批准,于是该法案在1980年代正式夭折,成为女权运动退潮而反女权运动阶段性胜利的标志事件。
回顾以上“反女权运动”的历史,一个反直觉的现象是,妇女群体一直是各类反女权运动团体和组织的主要力量——女性解放的阻力并非只来自男性。根据统计,保守势力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生命权运动”(Right-to Life)中,80%的积极分子都是女性,她们也认为自己才代表着美国真正的大多数女性。而女性也是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力军,最著名的反《平等权利修正案》领军人物为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她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美国夫人》(Mrs. America)。这些反对妇女运动的女性,除了有较强烈的宗教观念,也大多是依赖丈夫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或者是受惠于各种政策保护的女性。而在反堕胎运动中,女性群体的特征也很明显:根据统计,其中绝大多数人第一次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家庭主妇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80%为天主教徒,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家庭收入要低于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