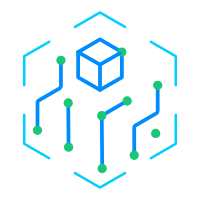严绍庭(严绍庭墓志铭)
严嵩柄政期间,京城内外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大丞相”指严嵩,“小丞相”指严嵩的独生子严世蕃。人们还愤恨地诅咒:“此时父子两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
>严绍庭(严绍庭墓志铭)
严嵩害死夏言、再任首辅时,年已七旬。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他年登八十,明朝阁臣实未尝有,皇帝特赐其岁支伯爵之禄,出入西苑乘坐肩舆。他执政日久,耄而智昏,精神衰惫,又日夜侍奉皇帝修仙,“竭赤匪懈”,故此无力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便将“事权悉付其子”,致使严世蕃“权倾天下”。
严世蕃狡黠机智,博闻强识,熟习典章制度,畅晓经济时务,而且精力旺盛,能任繁剧。尤其善于揣摩皇上的好恶喜怒,阳施阴设,无不中意。皇上时有要务相问,严嵩困窘不能作答,谋之幕僚,皆不称旨,而交之严世蕃,则引经据典,参综陈说,每获嘉奖。因此严嵩愈发依赖爱子,甚至将内阁大学士最重要的职权——为皇帝拟写圣旨(即“票本”、“调旨”)也交给他代办。他又召集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鄢懋卿等群会票拟,结成奸党。“一票屡更数手,机密岂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满朝纷然已先知之。”例如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皇上将奏本交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请教严世蕃。严世蕃乃同赵文华拟票停当,退交李本,李本照抄封进。即使弹劾严氏父子的奏本,也要由严世蕃票拟,“其余又可知矣”。
据说有这样一件趣事。嘉靖皇帝夜传圣旨,询问某事当如何处理,票拟颇难。严嵩与大学士徐阶、李本在值房仔细商议,每人各拟写一揭帖,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反复参酌修改,但终觉不妥,不敢誊清呈进。时已至四更,严嵩说:“当呼小儿来共评定,庶不忤上意。”便派人传请严世蕃速来。差人刚出,太监即来索取票拟,皇上立待回禀,已“嫌迟滞,有怒容”。严嵩犹豫不决,仍想等严世蕃来后商定。徐阶、李本说:“此事裁度再三,似已妥当,即使贤郎有高见,也不能超越于此,且上命严迫,难以再等。”严嵩不得已乃将三人商议的票拟誊录上呈。过了一会儿,严世蕃来到,见三人所拟底稿,连连摇头说:“未妥,未妥!”话音刚落,太监便将三人所拟揭帖拿回,皇帝朱笔涂抹多处,令再拟来看。严世蕃执笔重新拟写,上呈之后,皇帝果然满意,依拟照办。徐、李二公乃服。
关于严世蕃的暴戾和干练,还有一些传奇式的传说。他虽公事猥集,仍“饮食御女,日不暇给”。有时酒醉酣睡,恰遇严嵩有要事相询,便用金制脸盆,装满滚沸的开水,将手帨浸于其中,然后趁热提出,围头三匝,如此则醒,“无复酒态,举笔裁答,处置周悉,出人意料”。故此其父对之亦“慑服,凡有施行,俱不敢违,养成其恶,卒至诛夷”。
除代父票拟和为皇帝解答问题外,还要代父接见朝廷府部院寺大臣和地方官员,处理朝廷机务。朝臣向严嵩请示裁决,他则令其“与小儿议之”。起初尚问:“与小儿语未?”后来竟问:“与东楼语未?”(严世蕃号东楼,父在人前直呼子号为失礼)据说,若不见严世蕃,“严相亦不敢决也”。有时即使严嵩准许,而严世蕃不许,“卒弗许也”。因此相府之门每日如市,“庶僚之来谒事于小相者,肩摩踵接”。
严世蕃对诸大臣骄横无礼。朝臣拜谒议事,有终日不得见者,甚至有等三四日者,而且不敢流露出倦意来。即使是大学士徐阶、李本登门拜访,也要受到冷落和屈辱。他们来到之后,先要在厅堂等候许久,才会传出话来:“请缓之,中酒,需小卧乃起。”过了很长时间又传话说:“深酒不能起,以午未间(午时、未时)相见可也。”
对于阁臣尚且如此,对于平民百姓当然可以草菅性命。严世蕃铸制金、银、铁鼎,认为制造的“不如法”,便将铁匠陈连活活打死,事后只给银子十二两埋葬,而不受法律的制裁。
不仅儿子严世蕃以“小丞相”而操实权,即使老夫人欧阳淑端也干涉政事。太常寺典簿昝义金善于道家之术。欧阳氏染病,昝义金为之治愈,遂欲升其为太常寺丞。太常寺听命于礼部,严嵩便向礼部尚书吴山交办此事,严世蕃又命吏部文选郎中题奏。礼部祠祭司郎中徐学谟因其违反制度提出异议。严嵩乃对吴山说:“夫人意如此!”并怒骂徐学谟:“何物郎?乃梗吾家耶!”吴山劝说徐学谟不要得罪严氏父子,礼部遂奏准升任昝义金为寺丞。
严世蕃生子六,另有养子二人。他们皆因祖父、父亲而荫封官位。严绍忠诈冒军功,授锦衣卫镇抚。严鹄荫封锦衣卫千户,后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严绍庭荫封锦衣卫千户,后升至锦衣卫指挥使。严绍庆荫授尚宝司司丞。严鸿、严绍康、严绍庚荫授中书舍人。严绍庠例荫国子生,授后府都事、宗人府经历。锦衣卫负责侍卫、巡察、缉捕、刑狱之事;中书舍人负责书写诰敕、诏书等事,皆为皇帝近侍之臣。
严世蕃身边还麇集了一群门客。他们除了为其出谋划策、聚敛财货外,还陪其饮宴戏嬉,故又称为“狎客”、“私人”。除赵文华、鄢懋卿、万等人外,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份、工部侍郎刘伯跃、南京刑部侍郎何迁、南京通政司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禄寺少卿白启常、湖广巡抚张雨、广西按察司副使袁应枢、右春坊右谕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王材等皆与严世蕃朋党交通,狡佞无行。白启常甚至以粉墨涂面,引逗严世蕃欢笑。唐汝楫乃明代名臣吏部尚书唐龙之子,但却以父事奉严嵩,严嵩也以子畜养之。他可以直接出入严嵩卧室,关通请托,甚为世人所恶。严氏父子败落后,诸客相继罢斥,朝署为之一清。史家评论说,以鄢懋卿之干才,董份之文学,唐汝楫之门第,假若他们“持身克慎,恬静自守,皆可安坐而致通显”,但却“不自爱重,甘心为市井奴隶之行,卒之身名俱辱,为世所羞称,后来者可以鉴矣”。
严世蕃为求一笑,对门客恣意凌辱戏弄,门客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戏呼狎客王华为“华马”,王华便应声伏地,等候骑乘;白启常随即伏地作马镫,他遂蹬着白启常骑上王华之背,驱赶而行。一天,严世蕃与门客相坐,“适有余气(放屁)”。一门客厚颜无耻,用手搧拂着鼻子问:“何异香?”严世蕃佯装惊骇地说:“失气不臭者,病在肺腑,吾其殆矣!”这位门客也颇能随机应变,过了一会儿,又用手拂鼻说:香味已经没有了,只是“微有气”。严世蕃大笑,“以告所亲,盖亦轻之也”。
“宾客满朝班,亲姻尽朱紫”。严氏父子以血缘、亲戚、乡里、师生、门客、党徒结成庞大的权力网络,真可谓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宗法与封建政治相结合的特点。
严嵩父子败亡之后,人们在探讨其获罪的原因时,有的认为严嵩“为骄子(严世蕃)所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严世蕃蔑视国法,横行无忌,不仅使自己身陷诛戮,而且增加了父亲的罪恶。不过从根本说来,祸根还是在严嵩的身上。是他视权力为私物而委之于子;是他“溺爱灭法”,“纵子为非”,酿成“纪纲陵夷,廉耻扫地,边备懈弛,闾阎困敝,夷虏交侵,盗贼蜂起”的危机局面,结果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适足以杀其子”,断送了严世蕃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