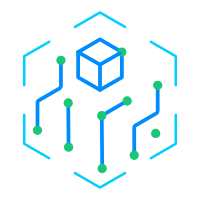徐继畲(徐继畲第三个字怎么读)
重温“同文馆之争”,当从同文馆的创办谈起。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将培养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
而甫任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更是不满于中央推行新政举措的过于迟缓,数次上书总理衙门,催促其早下决断。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谕令精于数学算术的南海邹伯奇、海宁李善兰赴京师同文馆报到,以资差委。这无疑传达了一种讯息:京师同文馆开始搜求算学人才,以筹备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用。至此,同文馆课程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徐继畲(徐继畲第三个字怎么读)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再次上书,进一步充分陈述添设天文算学馆的理由,并煞费苦心地预计了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上三折皆顺利得到谕旨批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太多阻滞。
二月十五日(3月20日),保守势力主将大学士倭仁披挂上阵,上折表示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他登场亮相,不啻是保守势力对奕??等洋务官僚发起的总攻。
倭仁开篇直奔主题,摆出了自己的立论基调:“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可谓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他又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倭仁认为诸如天文、算学不必师事夷人。其次,夷人是我国宿敌,断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倭仁立论紧扣“夷夏大防”之传统信条,以此展开攻势,切中了洋务派的要害。以倭仁的地位与学养,其言其论足以耸动舆论,朝廷对之极为重视。在奏折呈上的当日,两宫太后即召见倭仁。同时,将倭仁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初二日(4月6日),奕?上奏了长长一折,重申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缘由与苦衷。针对倭仁的汹汹攻势,弈?诸人避实就虚,绕开其奏折中关于“师事夷人”的追问,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体国之心。此外,奕?还指明了倭仁奏疏言论的危害所在:“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未等总理衙门奏折的墨迹变干,倭仁就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急匆匆再上一折,双方的第二回合之较量由此开端。篇首,倭仁继续抓住奕?等人不愿回答也无法回答的“夷夏大防”问题做文章。继之,倭仁又对奕?折中指责自己的言论会阻碍同文馆招生一事进行辩解。倭认为奕?此言实在过激。在篇末,倭仁抛出其最后通牒:“总之,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纡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
面对倭仁的又一波攻势,奕?等人的确感到些许措手不及。好在他们阵脚未乱,主持地方洋务的督抚们也纷纷致函总理衙门,加以声援,希望“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则事可有成”。经过一番商讨,奕?等人于三月十九日(4月23日)呈上一折一片,以示回应。针对倭仁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有无完全成功之把握的质问,奕?等人承认:“臣等只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是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明显底气不足。然而,奕?等人话锋陡然一转,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绽,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奕?进一步发问:既然倭相折中认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学之才,那么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选。所以还恳请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若能如此办理,更属两得之道,裨益匪浅,彼时臣衙门原请奏办之件,即行次第裁撤”。此建议立即得到谕旨允准。双方的争论达至最高潮。奕?成功地置死地而后生,转守为攻,将压力一并推到倭仁身上。
此时的倭仁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倭仁无奈地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这也预示着经过两回合的鏖战,倭仁已无计可施,败下阵来。此刻,两宫太后(当然以西太后慈禧为主)的立场也渐趋明朗,站在了奕?等人一边。既然两宫的态度已经明确,倭仁的厄运也随之降临。先是朝廷一再对其为难,奕?等人也有些得意忘形,继而落井下石。根据《翁同龢日记》,三月二十四日(4月28日),倭仁上朝请辞,与奕?口生龌龊,“几至拂衣而起”。同朝为官,奕?如此意气用事,步步紧逼,实在有失风度。
倭仁的退场并不代表论争的结束,恰恰相反,倭的狼狈遭遇却激起了保守人士的一致同情,不少人纷纷上书表示声援与支持,真可谓高潮虽过,余波未已。反观洋务派一方,自从击退倭仁之后,便无心再与其他保守臣僚多作纠缠,而是着手经营同文馆事业。
以奕?等人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呈奏疏为始,至周星誉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进折言事为终,“同文馆之争”横跨两年,延续八月,总计二百一十九天。细数这二百余天的论争,一浪接一浪,跌宕起伏,颇有值得回味之处。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推行改革政策之前,必定会综合考虑种种不利因素,以制定能够最大限度减少阻力的方案,步步为营,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而不是树敌无数,从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奕?等人确实欠缺火候,自始至终,一种焦虑的情绪在他们心中翻涌,其举措相对于当时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言,实在是显得过于激进与粗率。而保守一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眷恋与虔诚,也是合情入理之事,毕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扎根于此、受益于此,要他们承认自己文化上面的缺陷,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从头学起,不但是困难的,更是痛苦的。何况他们提出的一些关系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值得时人与后来者认真思索的。最终,论争双方两败俱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论战。
(摘自《领导文萃》2019年2月下)
稿件来源:《文史天地》